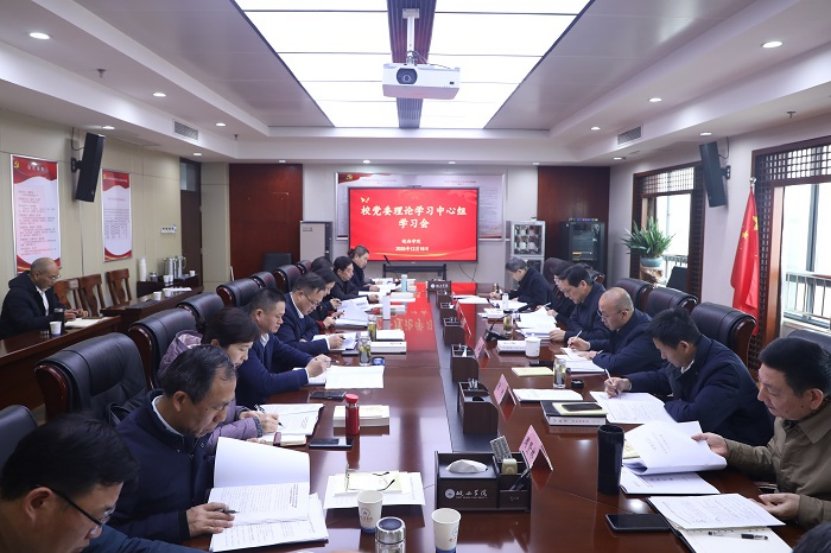年希属于八十年代
在一个教研室二十八年的同龄同事陈年希,突然走了。“突发性脑溢血”,刚刚在史铁生身上横行过,又从我们身边劫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好人。
追悼会上人山人海。年希的农场战友、工厂工友、大中学同学、同事、学生、朋友,来了这么多人。来送行者各自属于不同的年代,六十年代的中学同学,七十年代的农友工友,八十年代的同学同事,历年的学生子弟,迈入新世纪年希还到澳门、韩国教过书,可谓桃李满天下。这些人集聚在一起,见证了一个好人的成长、奋斗、进取直至熄灭的一生。我心里却响着一句话:年希属于八十年代。用更准确、更当下的表达,应当是“1980年代”。
初识年希,就在八十年代。1982年,我与年希几乎同时留校。我去拜访商韬先生,他也在。我看见的,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34岁,应该说不能算很年轻了,可当时我们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年轻。务农、做工,十余年就这么过去了。“知识青年”对于知识分子言,就是个“半成品”。如今,这一“半成品”终于在时代的恩惠与自己的努力下,完成了“精加工”,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成为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员了,新的生活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身边的景物都是那样的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那时候的我们,自与今天的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不同,我们心中的欣喜,是今人难以体会的。我们那时,有种劫后余生、九死一生的感觉。
年希就这样笑眯眯地站在我面前,新剃的头,胡茬青青的。那天都聊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反正聊得很愉快。
就这样,我们翻开了八十年代新的一页。我们一同去参加学术会议,怯生生地发出我们青涩的声音;我们一同报名到教师进修班学习日语,“亲(陈)桑”、“噢(翁)桑”地互相称谓;我们互相交流论文和报刊上发表的随笔,由衷地赞扬或带点酸溜溜的嫉妒,都有。八十年代,四个现代化正一步步向我们走近,商品经济尚未露出它残酷的一面,尽管还时不时地会有一些政治时代残留的口号忽然响起,但已是强弩之末,每每不久就归于销声匿迹。人们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继续努力,坚持奋斗,几乎是每个人的生命姿态。
年希的古代小说研究论文发表了,得到好评了,获奖了;他偶然“客串”的戏曲研究,也被收进年度论文集了。整个八十年代,年希的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的势头,都很好。
原本是可以这样一直努力下去、直至成为一个领域卓有成效的学者。可历史就在这当口,突然一个急转弯。记得我1990年从日本回来,惊异地发现系里的每一位老师,都有了兼职———年希除了教古代文学外,还必须兼教“公共关系学”。紧接着,是大学扩招、是非学历招生、是非学历不许招,是大学排名、学术造假……在时代的紧急转弯处,年希一定有过疑惑,有过迷茫,反正他学术研究的脚步,停在了八十年代的门槛里。
年希论文不怎么写了,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当他快乐的好老师。他课教得好,深得学生的爱戴。他教书育人,常常可以看到他站在校园里对着学生诲人不倦的身影。他在澳门上语文课,花心血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最后还为学生出版了文集,忙得脚也掮起来,我路过澳门想见他一面也不能够。年希的选择没什么不好。倒也清静,倒也纯粹。
年希属于八十年代,故八十年代也属于年希。年希唱的歌,都是那个年代的味道,八十年代创作的,或是八十年代重新唱响的。年希爱唱歌,五年前随学院去婺源,大巴上我与他同座,一路五个小时,我们差不多哼唱了五小时,把整个氛围都拽回到了八十年代。他会唱那么多的歌啊,让我惊呆。他说他常常腹诵歌词,不让自己忘却。
史铁生说:“死是终究会降临的节日。”或许年希也有相似的生死观,故他在与同事对唱了一首老歌后,转身就走了,走得这样义无反顾。他回到他的八十年代去了,却抛下我们继续磕磕碰碰地走在现世的路上。
也许我们整整一代人都属于八十年代。那个物质丰富起来却尚未泛滥成灾、人的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充满激情诗意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