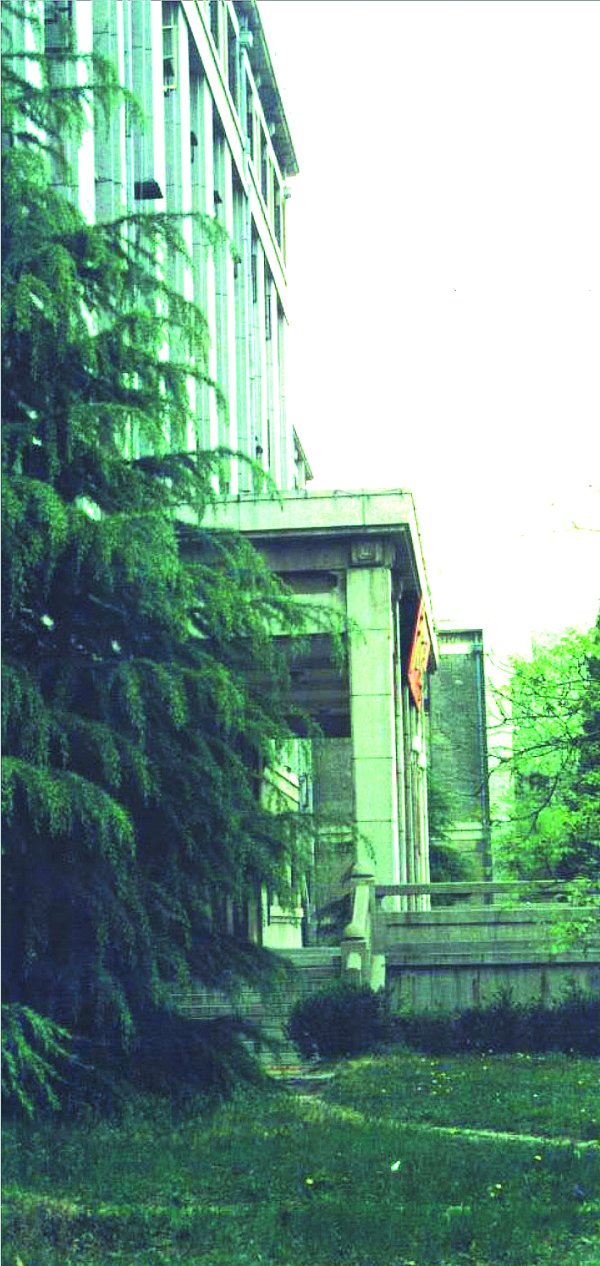
北航往事
1952年10月,薄暮秋风,从前门火车站出发的敞篷卡车载着我们这些报到的新生缓缓驶入清华园,停在北边距圆明园仅一步之遥的七宿舍附近。车门打开,一位身着“布拉吉”式黄军衣的退役女兵,满面笑容接过递下的背包行李,并且帮我们找到床位,这样,在寒意与热情的交织中,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
我被分配在航施106班,其中的“施”表示清华航空学院的这十个班全部被指定学施工的专业。我那时的字迹潦草,书法零乱,以致我家来的信封上,“施”全被误导成“旋”,这种错误又延续至航“旋”105班,直到二年级进一步分专业,不再使用这类班名为止。
我本对无线电很感兴趣。报考航空,与国家当时正面临抗美援朝的形势有关。因为小时有目睹日机轰炸贵阳整个投弹过程的经历,看到我方高射枪弹的爆烟都在敌机下方无可奈何的场面,造飞机,打敌人成为心目中自然的第一选择。当然,那时并不知道国防也需要无线电技术,否则就不学航空了。
在航空馆参观飞机座舱,各种仪表令人眼花瞭乱,很感兴趣,如果那时设有仪表或者控制方面的专业,我肯定会去报名,而“施工”的专业,以前从未听说,那时介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例如讲飞机的蒙皮用特殊的材料打磨之后,阻力可以大大减少等,我很感兴趣。进一步分专业的时候,只有飞机施工和发动机施工两个专业可供选择。我报发动机,是受到在航空馆看到外国杂志上零件图片和在军工厂参观实习的影响。图片上,那些被加工出来的发动机零件看上去形状复杂,玲珑可爱,光洁精良,个个都像令人不忍释手的宝贝,心想如果能从事这样的工作,其乐必定无穷,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工厂,我很高兴,但是没想到,一年劳动锻炼刚结束,即让我去工厂的产品设计部门工作,就此终生与发动机的设计工作结缘,直到如今。
北上的列车始发站是长沙,至少有三分之一个车厢装运着当届北京高校新生。40多年后,我去单位招待所看望时任航空学报编辑的许昌淦,适逢他当时外出。与同屋者攀谈,方知对方为西工大教授胡光立,也是我们这一届校友,他四年级时抽调到新设材料系读研究生,而且他还竟是当年长沙市学联组织我们那一批人赴京学生的领队。但在那以后,因为分班分系种种原因,再未谋面,使我感到惊奇不已。人之因缘聚会,竟然如此!
我们这一届,调干生特别多。他们虽只稍长我们几岁,但已有参加革命的各种经历。阅历见识、人生经验、思想修养等各个方面比我这些纯学生娃都要高出一大截。其中,既有来自曾经跨过鸭绿江,头戴三块瓦军帽,身着短军大衣典型打扮的前志愿军。也有穿兰灰色四个兜上衣或列宁服的中央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前干部。他们同样是普通的学生身份。上课,交习题,考试不及格时一样要补考甚至留级。一二年级时,是全部实施当时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的教学计划,功课特别紧,习题也特别多。一周实际上只能休息半天,打点洗衣理发之类的事。就是我这种能够安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也常感力不从心时间紧张,但调干生中的许多人还要从事班级以至系内的许多社会工作。找同学谈话搜集对学习的反映,组织文体活动,发展党团员,无一不需支付额外的时间与精力。与我同班5年的汤宁来自中央组织部,就是一位典型的调干生,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她像个大姐姐对你严格要求,但从来没有性急的指责和对个人人格的轻视,总是不断地鼓励并观察等待你认识上的提高和进步。她对青年人思想斗争规律的了解与掌握,那种有血有肉的中肯分析,一定来自她对自身的严格剖析和丰富的社会实践,我还记得她花了不少时间给我的棉袄动过一次不小的手术,修破翻新。令我这种远离父母、从不愿开口求人做事的人心中不胜感激。千层单不如一层棉,要知道北方严冬在无任何供暖的小平房和四处透风的工棚教室内,一件完整的棉衣是多么地可贵!
刚到北方,我们这些“南蛮”,说不好普通话,更听不懂京腔土语,闹过不少笑话。北京人称鸡蛋为“鸡子儿”,称“用”为“使”。邓家褆曾对我讲,他到小卖部买在南方称“皮蛋”,而北京称“松花蛋”的东西,开口要买“皮子儿”,人家说没有。又比如盥洗室内共用搓衣板,为了谦让,说“你用我不用”为“你使我不使”,南方学生多“sh”、“s”不分,结果互说“你死我不死”。我去理发,被问,大点还是小点?说不明白,最后干脆请他剪光,剃成那时在南方称为“球头”的式样。
入学的头半年,生活环境,学习内容方法无一不存在新的变数,冲击和考验着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在别人看来,我一定不是个好学生。原因是:第一,我仍然在沿用小聪明式的读书,学习不刻苦,随意应付。那知功课门数太多,作业也重,不下真功夫绝对不行。第二,对提倡大学生独立思考理解错误,以为凡事都是由自己从头开始去推导论证,完全撇去老师课堂讲授。这两种似乎有些矛盾的因素对我作用的结果是觉得不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习题负债与日俱增。我不喜欢画图,总感画出的太阳不象,又不知为什么。一直到十几岁才恍然大悟,原因是我画的光芒线没有通过中心,以我这样的素质,遇上一般人都有点打怵的“头疼几何”更迎来数不清的麻烦,没有一次习题课能按时完成。拖堂最后一个交卷都是家常便饭。其实这中间也有认识上的误区,因为老师讲要建立立体概念,所以坐在那里傻想,比方那些相贯线究竟是怎样交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而不是别样?钻了牛角尖。最丢人的一次是老师讲可以用两块三角板推画平行线,但未仔细示范。大概天气寒冷我手指左推右推就是推不出来,不大灵活也有点关系,最后终于发问:“老师,这平行线到底怎样推呀?”年青的助教狠瞪我一眼,叫我看着,如此这般,“会了吗?”令我大为羞愧,怎么这样简单的事我也想不到呢?那学期的考试复习我记得在图书馆把投影几何的那本教科书认真读了一遍,并且边看边画,悟出无论什么复杂的图形投影无非都是找几个特征点作平行线,在几根代表投影面交线的直线上等半径地转换位置后,再作平行线,找出与另一组平行线的交点,将这些交点连起来就完了。看起来最难的相贯线求法也是大体如此。接下来的考试非常顺利,除一道小题外,全部作完作对,如果不会推三角板,断然不会有此结果,不耻下问还是有收获的。只是后来听说,老师讲这个学生平日成绩太差,考试中基本题又有错误,给他个 “良好”吧。我当然无话可说。只是未能完全咸鱼翻身,有些可惜。
举一反三,从错误的实践中汲取了教训,学习慢慢上路入门,逐渐有了一些主动权。三年级时,材料力学荆广生教授极力推行课堂重点讲授基本概念,其余内容课下自行学习消化的方法。两节课内他只讲占三、四页书的内容,课下自己要看2~3倍的内容。记得他讲,如果你们能坚持这样做下去,以后会受益无穷。联系我初时的经历,对他之言,深信不疑。现在回想起来,确是无穷受益。这就是具备了较强的自学能力,可以运用最基本的知识去扩大自己知识的范围,去解决各种事先并不了解的新问题。我在以后从事的各项专业工作中,绝大部分的新知识,包括理论知识,都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母校几年的教育,不仅给予我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获取新知识的造血机能和赋予人去主动掌握知识的基础,令人一生受用不尽。五年前,毕业于飞机施工专业时任沈阳航空工业学院教授的张法荣同学赠我一册他的文集,包括论文和各种形式的著述近70篇。内容涉及天文,近代数理,制造工程,经济管理,领域之广,知识之博,思考之深,工作之勤,令人赞叹。在与他相比看出自己鲁钝的同时,更是感到经过母校同样过程的培训教育和个人自身的刻苦努力,一旦爆发,可以产生多么巨大的能量,可以多为国家和人民作多少事情。张法荣同学长期身处逆境,仍潜心钻研、自强不息,困境崛起、笔耕不缀,实是我们这届同学之中的佼佼者,也是彰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优秀品质的楷模。我在为母校成功地培养人才而欣慰的同时,也痛感社会在珍惜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曾经发生过的缺失与错误而惋惜。
同样在不知不觉之中,斗转星移。毕业之后,半个世纪已快过去。当年最年轻的“小鬼”们也都年过七旬,鬓发皆白,为人之祖。但五年的校园生活,那些风华正茂、同学少年的形象仍不时浮现眼前。在多达数百之众的同学中,在校时有的是朝夕与共,有的仅为萍水相逢,还有的是从未相识或有过只言片语。毕业之后,多数是聚而复散,就此天各一方,再未谋面。但却也有少数是散而又聚,或旅途会议相逢,或又从天南地北调至同一单位。这些都不再要紧。无论以往是熟识或生疏,无论今日尚留尘世或已驾鹤西去。我们都曾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喝着同一个桶里的汤,吃着同一口锅里的饭,面对着同样的喜怒哀乐,彼此之间施放着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共同演绎着成长的历史,也共同承担了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分享家庭、事业上成功的喜悦与人生历程中的苦涩与酸甜。我牢记这弥足珍贵的友谊与精神财富,衷心感谢包括在清华一年的母校的培养与教育,对每一位教师和同学致以深深地祝福和怀念。 (校友会供稿)注:作者曾任职于中国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我校1952级校友。
(凌天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