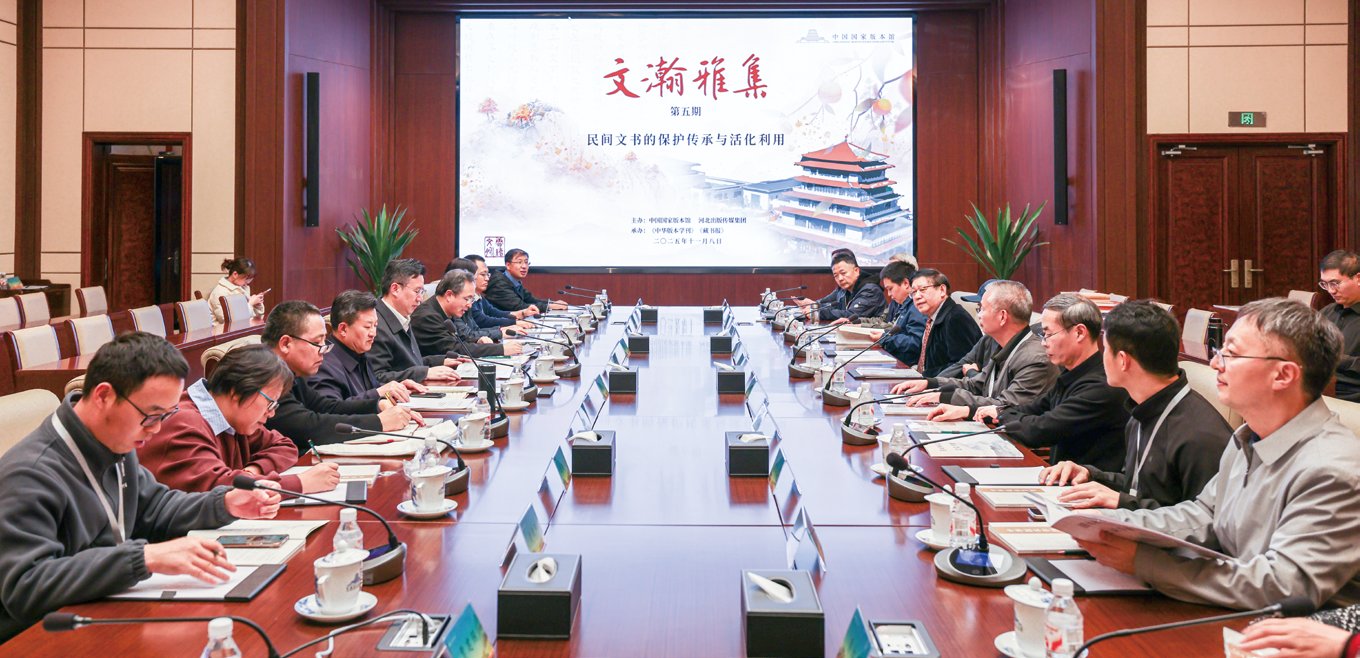-
第277期
刘家和先生口述史(十一)
巧学外文
我刚工作时,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安排的专业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当时自己很想进中国古代史专业,但既然是工作的需要,当然也就服从了。
做世界史,要求外文好。我当时只是会一点英文,能看一般的英文历史书籍,但是阅读速度与理解深度都很不够。好在我对外文不仅无反感,而且有兴趣(早年不愿意学日文是另一回事)。既然要我搞世界史,那就横下一条心学呗。正在加紧提高英文水平时,又遇到了必须学而且要迅速学会俄文的要求。英文还未及加深,又来了俄文,搞不好就会“鸡飞蛋打两头空”。怎么办?于是我又参加了突击式的俄文速成班,班上老师要求学过一种外文的人尽可能联系已学的语言来学俄文。这给了我一个大启发———联系英文学俄文。
我的办法是,准备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两个本子一字一句地对照看,每一句都用在中学学英文时的图解法(diagram)来做文法分析,用不同颜色的铅笔轻轻地划在书上。每天不求多,但必坚持。经过一段时间,这本书读完了,自己觉得效果还不错。
又用同样的方法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到这本书读完,不仅没有了“鸡飞蛋打”的顾虑,而且感到这样做能够使英文与俄文的学习互相促进;特别是在对读过程中发现了印欧语言词汇、语法中的一些有趣的异同,很开眼界。以后,我学德文,到自学阶段时还是用这个方法,用德文原本对照英文和俄文译本,每句都表解分析地读。由于德文和英文关系更近,在比较对读中可以迅速发现二者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异同,大大加快了德文的把握进度,而且对三种文字的学习也大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同时,收获还不仅于此,这样做也使我更自觉地在学习中注意比较方法的运用,促进了我的比较意识。
随着比较意识的提高,我也把学中国古汉语文字学的方法运用到学外文上来。对汉字,我有追寻其小篆字形和古音的习惯;推广到学外文上,就是随时追寻外文字的字源。这种方法短时间看不到效果,成年累月积累下来,就很可观。它既有利于加深、加固对某一种文字的理解和把握,又有利于学习多种(同一语系)的文字。还有一个原先没有想到的效果,就是因为理解得深,所以记得快、准、牢,从而大大提高效率。原先以为这样的笨方法会费时间、低效率,而结果恰恰相反,尤其从长时期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正是因为这样,尽管我曾费了大量的时间学外文,但是学外文并没有妨碍我对中国学问的学习。
我注定要做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了,就决心好好干。当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正热,有些先生涉及了与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制度的比较。我想,要研究希腊社会经济问题,斯巴达和雅典总是不可缺的。于是就开始准备做黑劳士制度的问题。这时东北师大来了一位教世界古代史的苏联专家,要开青年教师进修班。我考上了那个班,从1955年深秋到1957年夏,在那里学了两年世界古代史。这两年里,除专家讲的本专业课外,还有俄文及理论课,其余时间就是做论文。我就选定了《论黑劳士制度》为题,结果写出一篇八万多字的论文,其中涉及了与中国史对比的问题。论文在一个规模不小的答辩会上答辩通过,并得到了当时认为的最好的评价。进修班毕业,可是没有颁发任何学位;全班同学也都没有获得学位,当时没有这个规矩。一位老先生把此文推荐给了一家出版社,他们看了稿子,答应出版,但是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多数文字加工意见我都能接受,就是有一条我不赞成一位苏联大学者的意见的地方,他们要我必须改;我想我的苏联专家老师都没有要我改,宁可不出也不改。这样就没有再把稿子寄回给他们。我算做对了一件事:没有把不成熟的东西随便发出去。
做《论黑劳士制度》论文时,我一直有两块心病。一块心病是只能看洛埃布丛书的英译文的这半边,而不能看其希腊原文的那半边。用史料不能从原文入手,怎能算真正的研究呢?另一块心病是,眼看着要做比较研究,可是自己在中国古史方面的文献功力仍然显得不够。
由于想治这两块心病,首先打算自学古希腊文。找了一本用英文写的希腊文文法书,自己就试着往下学;因为没有老师可以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下来的问题无法解决,最后只好放弃。学不了古文字,就转而自学德文。我买了一本北大德语教研室编的《大学德语课本》(第一册),自学起来。毕竟现代语言比古语文容易多了,这次自学为以后几年从师学习德文打下了一个初步但扎实的基础。
古希腊文学不会,就更觉得自己不能放松在中国古文字方面的努力,因为这是我在可望的将来(现在应该说终身)能够直接用来研读原始古文献的唯一的语文了。自从工作以后,尽管具体做的是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但我从未间断在中国文献方面的业余学习。最有保障的是一天工作下来的晚饭前或后,到住处附近的旧书店去逛一个小时左右,除一般寻找有无可购的中外文书籍外,每次的重点都在搜寻清人的小学、经学和目录学方面的著作。有些书很贵,买不起,就每次看一些,总要看到有一个大体了解才罢手。对清代著名学者年谱,每见一部,都要浏览一遍。这样就逐渐积累了一些最基本的清人小学、经学著作。
我买书的原则是,在买得起的里面挑版本印刷最好的,但也没有名贵好书。我常对人说,自己买书几乎像旧社会挑女婿一样,左看右挑,经过许多回才很吝啬地买一本。其实不是吝啬,这样买来的书,未到家,你对它的大体内容、功能特点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以后用起来效率高,有时一本能顶好几本用。这一点可怜的体会,也许是有钱大手大脚买书的人无法感受的。直到“文革”开始前,我这一逛旧书店的习惯一直坚持十几年不断。“文革”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又同时兼做中国古史教学与研究,之所以不觉突然,实在与此有关。(整理/雪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