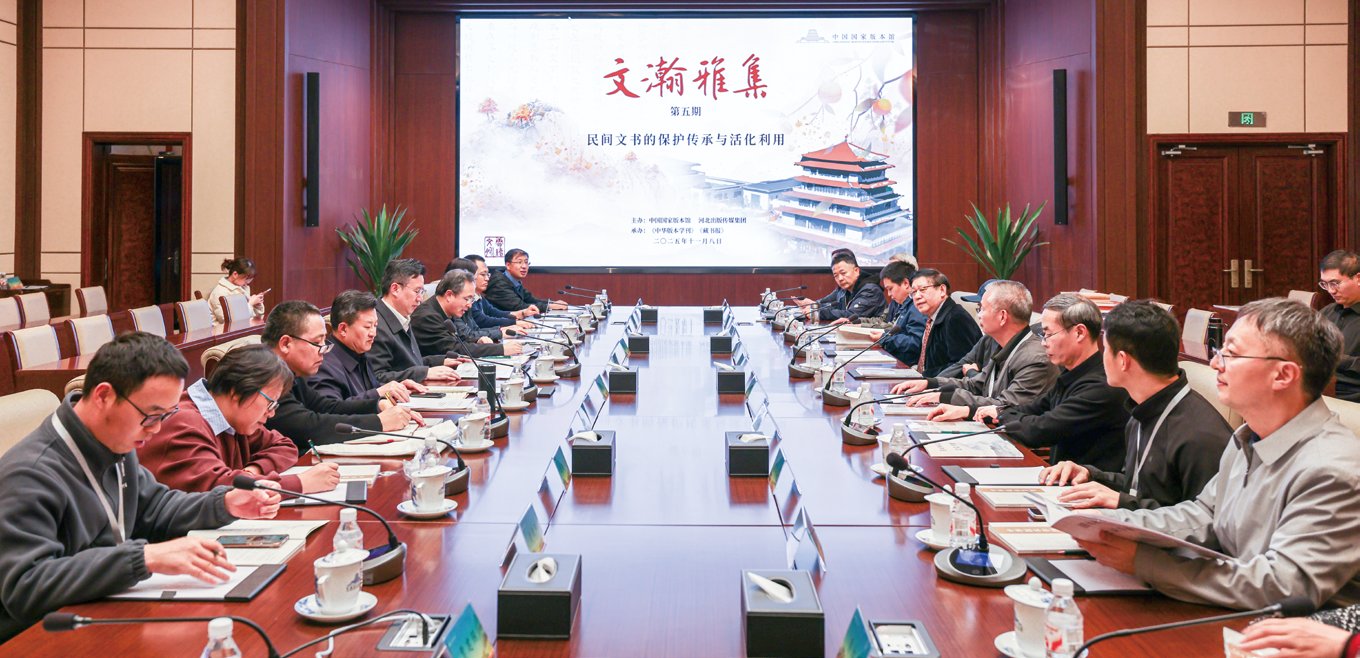-
第215期
父 亲 的 节 日
79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听到村里人成分不好也可以考大学这个消息时,三十二岁的父亲,正熟稔地跟在那头倔强的老牛屁股后头深深浅浅地犁田。欣喜若狂的他,犁头一扔,将满是泥泞的脚从田里拽出来,冲到县城—他赶上了那年高考的班车。发榜后,成为省城孕育了毛主席的那个学校253班年纪最大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为了母亲,父亲放弃留校机会,回到家乡,成为一所县城高中的老师,成为一位众口皆碑的好老师。
从开始更事的记忆中,每到教师节那段时日,家里的电话成为父亲的专属热线,而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贺卡,信笺,更会源源不断飞到家里,久而久之,积累了满满的大麻袋。每每见了父亲,悉心地读着那些真纯的话语,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
实在地说,父亲真的是一位凶狠的老师。他上课,必然随身携带教鞭,那种棕黑的粗粗的棍子,哪个学生不认真,讲小话看小说睡觉,他会过去就是一下;他当班主任,不管炎夏寒冬,每天六点半必然定时去宿舍喊学生起床,站在宿舍门口威严咳嗽一声,等三分钟擂门,再就是直接掀被子,不管你是男生女生,让你瑟瑟的惊醒。
所以,我每每不明白,为什么那时他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学生们愿意被他打被他骂而不还嘴不还手,反而只会更惧怕更尊重他。再调皮的孩子,远远看到他,都是双手垂下来,毕恭毕敬喊一声,银老师。我的家里,从来是门庭若市,坐满了父亲的学生,来我们家热热闹闹吃饭,聊天,亲亲热热帮妈妈干活。如果换了今天,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我和母亲一直好奇和担心了很多年的事。总是生怕那些孩子们冲动之下,对着父亲挥舞起忿怒的拳头。然而一直都没有。直到后来听见他的学生们亲口这样说,我们心里都知道,银老师是为了我们好。
一直记得有个姓马的男生,家境不错,从小也养成了跋扈飞扬的性格,爱打架,脾气暴,但是唯独惧怕严厉正直的父亲。高二时,终于出事了。在外面惹了一帮小混混,对方几个人,举着刀械吵吵嚷嚷找到了学校。他抖抖索索跑来,找到正在家里吃饭的父亲。父亲没做声,带他进卧室,关了门,一巴掌过去,扇得他当场蹲在地上。然后父亲扛把锄头出去了,走前把家里的门锁上,丢下惊惶的母亲和我们。父亲站在那帮小混混面前说,你们要砍我学生,先砍我。你们砍了我,我的学生们都会上,你们跑得掉吗?父亲的冷静和正气,镇住了那帮小混混,他们骂骂咧咧悻悻然走了。
从此,那个男生,静下心来读书。毕业后,参了军,当了士官。再后来,转业回家乡,进了政府部门,混得不错。去年暑假,他结婚。带着新娘子,坐很远的车,专程到家里,接父亲母亲去参加喜宴。在喜宴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这是我的老师。没有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还有那个姓罗的男孩子,那个姓李的女孩子……原谅我,关联的人和故事太多,而我的记忆过分简陋,笔头又太拙钝。
父亲或许算得上我见过的最勤奋扎实的读书人。他的一生,除了喝喝酒抽抽烟,其余的时光,便都贡献给了桌前那盏白炽台灯,还有案头上那沓沓厚厚的书。历史,政治,天文,地理,文学,当然,更多的,还是他的本行———英语。因为他,我最开始意识到,原来是真的,有如此从本心里,而不是为着某些目的,热爱着知识热爱着学习的人。
印象里,无论孩提时候,还是长大成人偶尔归家,半夜朦胧中醒来,让人安心的,总是他案头那盏灯泻下的柔白光芒。而他伏案的瘦削身影,一直成为心里永恒不灭的长明灯,支持我提醒我永远不要轻易停息,往前走下去。几十年如一日,每天五点,他都是铁打不动要起床的,窗外清冷的鸡鸣声中,一杯冷开水喝下肚,然后拧亮台灯看书。他从来坚持认为,三早赶一工,早晨,一定不能荒废。也是他的遗传与身教,令我养成不赖床不贪睡的好习惯,再放假的时光,再轻松的日子,都会定时在六七点起床,呼吸新鲜空气,畅想光明未来。
他是如此醉心于自己的专业。他的大大小小的教科书资料书,他的一沓一沓厚厚的英语试卷,他的一本一本大部头的英语字典词典,都做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光那手飘逸隽秀工整的字,看着就是享受。我读大学时,寒暑假回家他拿着我的大学英语教材攻读整个假期;我上研究生时的英语教材只留给他;我用来考博士的英语资料,也成为他孜孜学习的素材。从他那里,我真切意识到,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不仅仅要有一桶水。是的,他对学生的,便是这样尽责到极致的态度。常常为了一个小小的语法知识,要来去查几本书,要满满做几页备课记录。
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父亲内敛木讷,母亲精明活泼,两个人性格极般配,母亲当家几十年,父亲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工资卡密码几多,平日里母亲做的饭菜,他从不准我们挑鼻子竖眉毛有一丝的挑剔,更不用说到了今天他们一旦分开,每天数个电话的柔情蜜意。
然而,他们唯一一次激烈的争吵,却也是为了学生。
那时父亲的很多学生从农村来,家里穷,每到开学总交不起学费。父亲是班主任,催缴学费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他从来忍不下心去找孩子们讨要,于是总是和学校说,从我工资里先扣着吧。就这样,有个学期一开学,父亲一个月几百块的工资,就被扣到已经见光,而那时,我和妹妹两个人要上学,要长身体,家里正是要钱的时候。
母亲终于生气了,要父亲去学生家里讨学费。父亲不答应,说人家有钱还用欠学费吗。母亲委屈了,人家没钱,我家就有钱了吗。铁了心,只是逼父亲打电话。父亲依旧沉默,不打。僵持中,母亲让步说,我来拨号码,你只要说话就行。父亲仍只是说,不行。母亲是真怒了,逼问父亲,你打不打?你不打,我就来打。我自己说。
我现在仍记得父亲当时的模样,铁青着脸,太阳穴边的青筋一跳一跳,很可怕。沉默得滴水的空气里,他忽然三步并作一步,冲到屋角,拎出锄头,对着电话狠命砸下去,惊天动地的声音中,电话粉身碎骨。母亲一下就懵掉了。
我也仍记得那天,父亲一根一根坐在沙发上抽烟,母亲一直一直在伤心哭泣,而我和妹妹,瑟瑟地躲在角落,充满了忧伤和惶恐。那是他们之间最为暴烈的一次战争,之后便再没有过。因为,母亲再也不会提类似的要求,而父亲,也会小心翼翼地避过。但是,现在我想,父亲之所以当天做出那样激烈的举动,是因为他的心里,既充斥了对学生的不忍,又充盈了对家庭的自责,还有更多作为一个师长,一个男人,面对现实困境的无力。几相激荡,那样的失态,也是可以理解和谅解。
现如今,六十多岁的父亲,还是放不下课本,放不下学生,受学生之邀,携着母亲千里迢迢跑到贵州去教书,成为那里最受欢迎和尊重的骨干教师。生活清苦点他不怕,儿女们劝说回家享福他不听,只是乐呵呵,每日里耐心为着那一群孩子,倾囊相授着自己的学识,想要尽力让更多的学生跳离那个穷困的地方,去到更好的大天地新世界。
我们做儿女的,也唯有默默为他祝福,祈祷。也唯有在这一年一度的九月十日,诚挚道一声,父亲,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