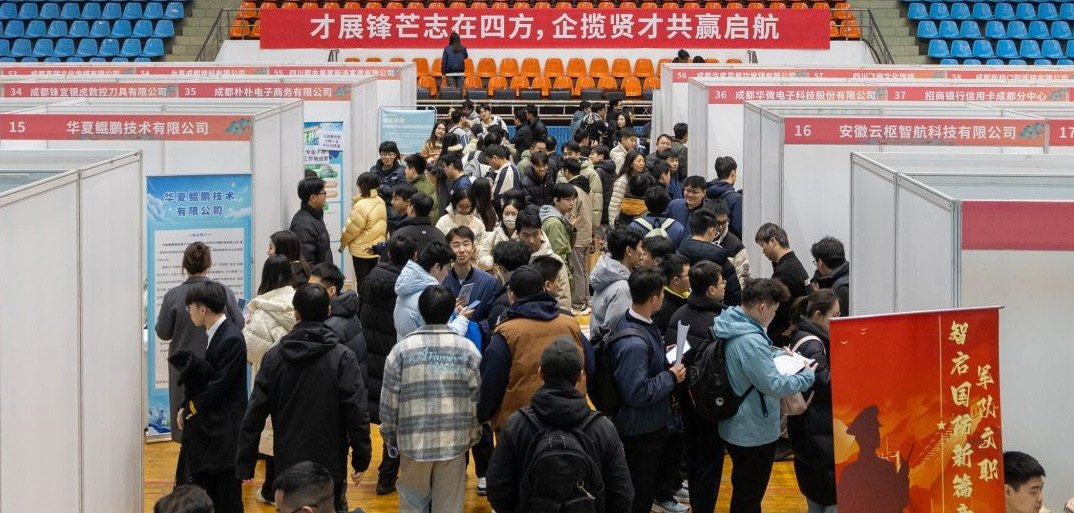两小吴拆
大米一家迁到我们村的时候,刚好是那年的秋收时节。玉米连同杆变得一身金黄,在阳光下显得有些刺眼。玉米棒像一个个大肿包,稳稳地扎在杆中央,它们大都被玉米叶包着,裹得严严实实。偶尔有一两个脱了几片叶子,露出鲜亮、饱满的玉米粒儿。南瓜经过整个夏天的疯长,现在已长到了极点,顶着个大肚皮安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它的主人来把它带走。一大群蜻蜓在玉米地上空飞舞着,举办他们冬眠前的最后狂欢会。
大米一家刚进村的时候,我母亲正背着背篓,前面顶着还没出形的我,在金黄色的玉米地里忙得欢,看着田埂上走过的一大家子,对身边的父亲喃喃道:“那谁呀?”
父亲随意瞟了一眼,说:“你管他谁呢。”
我和大米都出生在第二年的夏天,大米比我早出生一个月,这样即使我们活到一百岁,大米还是大我一个月。
我和大米是形影不离的伙伴,我们一起做坏事,也做好事,但更多的是无聊的事。
我们喜欢在一起扮家家,大米家有一条鲜红色的被单,每次我们扮家家大米都把它带来,连同身子把我盖起来。我家的大枕头就是我们的孩子。一次,大米说:“叶子,枕头比你还大,不像。”
“那该怎么办好呢?”我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下,问道。
“我看看。”大米转过身去从旁边的土里抱来一块石头,说:“就用这个吧。”
大米抱着石头,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接过来。但一不小心,大米没抬住,石头掉了下来,不偏不倚刚好砸在我的脚上,正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哇啦哇啦地大哭起来。
每次我去找大米玩的时候,总喜欢大呼他的名字:“大米,大米———”。如果大米正拨弄他的泥鳅:“你咋呼什么呀?把我泥鳅吓了。”
我说:“你陪我去粘蜻蜓,我给你糖吃。”于是大米就陪我去粘蜻蜓。
初夏的秧田间,蜻蜓窜来窜去,有鲜黄色的夏金,蓝色的泡桐,黑色的鬼王,淡黄色的朝网,小个儿的玉米。最珍贵的要数夜老水,它只在夜晚出来,白天藏在竹叶间,我和大米去竹林间粘过几次,只粘到过一只,它的尾巴很长,翅膀透着微黄,两只眼睛又大又亮,很漂亮。最容易粘的是小个儿的玉米,它飞不一会儿就会停下来,一停就是大半天,有时用手都能抓住,不过它太小,我们不粘它。最难粘的是朝网,它飞两三个小时都不停下来,我们也不粘它。
大米不喜欢陪我粘蜻蜓,他喜欢下田去捉泥鳅。他一下田,我就去吵姐姐。
姐姐大我八岁,她怕我去吵她,尤其是她做作业的时候。她用零花钱买了一大包泡泡糖,我一去她就给我一颗,把我打发走。
我再跑去找大米,大米说:“你有糖吗?”
我说:“有,但是只有一颗,被我吃了。”
大米很失望,说:“好吃吗?”
我说:“好吃,我现在嘴里都是香的呢。”
大米说:“那你让我闻闻你的嘴,闻了我就陪你去粘蜻蜓。”
然后我就踮起脚尖让大米闻,大米闻了就去拿竹竿。
村里人不喜欢大米的父母,尤其是大米的父亲,村里人都侧着眼睛看他,就像看一只没有尾巴的狗或多一个奶头的母牛。
大米的父亲是个老实的农民,他不爱说话,总是嘴里含着一根烟,“吧嗒吧嗒”地吸。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他,为什么要议论他,尤其是女人,一大堆的女人,我听不懂她们说什么,我只记得一句话,那是东头二婶说的,她说“那个倒插门儿的”。
我跑去问母亲“倒插门儿”是什么意思,母亲说,是门闩。我百思不得其解,好好一个人,怎么像门闩呢?
大米的母亲是我邻居大公的女儿,我该叫她姑,但我很少叫她。我觉得她很凶,她常和王婶吵架,王婶是大米的舅妈,她们一吵就是几天几夜,有时还打。有一次,她们在玉米地里打了起来,把整块玉米地都滚平了。
大米的母亲很会生孩子,加上大米她共生了七个孩子,死了一个,还有六个。加上两个大人,就八口人,足足是我们家的两倍。村里哪家办酒席,他们一家就占一桌。
有段时间我们家母猪下了崽,母亲不让我去玩,叫我去放猪,大米就陪我去。
那是暖春季节,阳光很温暖,山坡上长满了草,绿油油的一片,很漂亮,踩上去舒舒软软的,像一块天然绿地毯。草丛间还夹着些五颜六色的小野花,散发淡淡的香味,很好闻。
我和大米坐在草丛中,望着蓝天上飘过的雪白雪白的云,陶醉其间。大米说:“好白的云啊!像花一样,真好看。”
我说:“不对,花不是白色的。”
大米说:“有白色的花,像梨花。”
我说:“梨花没那么好看,还是我姐说得好,她跟我说,天上漂浮的云,就像是一团一团雪白的棉花。”
大米想了想,说:“嗯,你姐是说得好。”
我说:“我姐说,这叫比喻。”
大米说:“什么叫比喻?”
我说:“就是什么像什么。”
大米家没有大米,因为他们家没有田,只有两块地,都是大米外公悄悄给他们的,为此大米母亲和大米舅妈又打了一架。大米家一年四季都喝玉米粥吃咸菜,因此大米喜欢到我家来蹭饭吃,因为我家的饭里加了少许大米。村里人不喜欢大米的父母,也不喜欢他们家的孩子,我父母是唯一没有歧视大米他们的人,那倒不是我父母素质高想得开,而是因为我家就我和我姐,没有男孩,就这一点,也足够让我父母在村里不敢大声说话。同是不敢出大气的人,也就没有了歧视别人的心气与资格。
我和大米的关系很好,但我们也吵过,最厉害的一次是为了我姐。
那天我姐给我买了个气球,我把它吹大,用线绑着去找大米,我说:“大米,你看,我姐给我买的气球,好看不?”
大米说:“我不看,你姐坏死了!”
我说:“我姐她怎么了?我不许你这么说。”
大米撅着嘴说:“你姐骂我们,说我们是两小吴拆。”
我问:“两小无猜是什么意思?”
大米说:“我们那边有个人就叫吴拆,他什么都不做,懒死了,所有人都不喜欢他。他很老了,但还没有媳妇儿,没人愿跟他,你姐这么说,就是说我们懒。”
我反驳,我说:“不是的,大米,你胡说,我姐不是那样的人。”
大米也生气了:“她就是这个意思,叶子,你和你姐一样,也坏死了,你会变成妖怪的。”
我气爆了,母亲讲的故事里,妖怪都是极坏极坏的东西,也是我最讨厌的东西,没想到大米竟会这样说我,我“哇”地一声就哭了,指着大米骂:“死大米,烂大米,你就算叫大米,你也一辈子吃不到大米!”然后我就跑了,那次吵完后,我们五天没有说话。
七岁那年的秋天,我背着书包去了学校,成了一名真正的学生,大米很羡慕,站在门槛前眼巴巴地看着我,看着我走过田埂,消失在村口的小路上。
大米的父母也想让大米去上学,大米的五个姐姐都没有进过学校,他们家辛苦攒了大半年,快要凑齐学费了,但大米母亲的一场病,让大米上学的愿望泡了汤。我的学费是父亲与母亲磨了一个月的玉米面换来的。我现在觉得,我和大米生在了一个倒霉的时代,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是不要钱的,现在我读大学了,读小学不要钱了。如果我们生对一点,我们就能轻轻松松上学了。
大米父母说,明年去上学,大米就跑来告诉我,说:“明年我也去上学,我们一起去上学。”
我说:“好,我等你。”
可是,我终究没等到那一天,终究没能和大米一起去上学。
大米家搬走的时候,依旧是在一个收获的时节,过不了一个月,就又要开学了。但是,他们走了,是在大米母亲又一次和大米舅妈打了一架,大米舅妈连续骂了三天三夜之后,大米父亲狠地抽出嘴里的烟,“啪”地一声扔在地上,对大米母亲说:“快收拾东西去!”
大米家走的那天,我在山坡上放牛。天空碧蓝碧蓝的,蓝天上飘着一团一团的白云,我远远地看着他们走向田埂,一大家子,浩浩荡荡,最后消失在村口。
我抬头望着天,一团团的白云飘过,我觉得姐姐说得真是好极了,天上漂浮的云啊,就像一团一团雪白的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