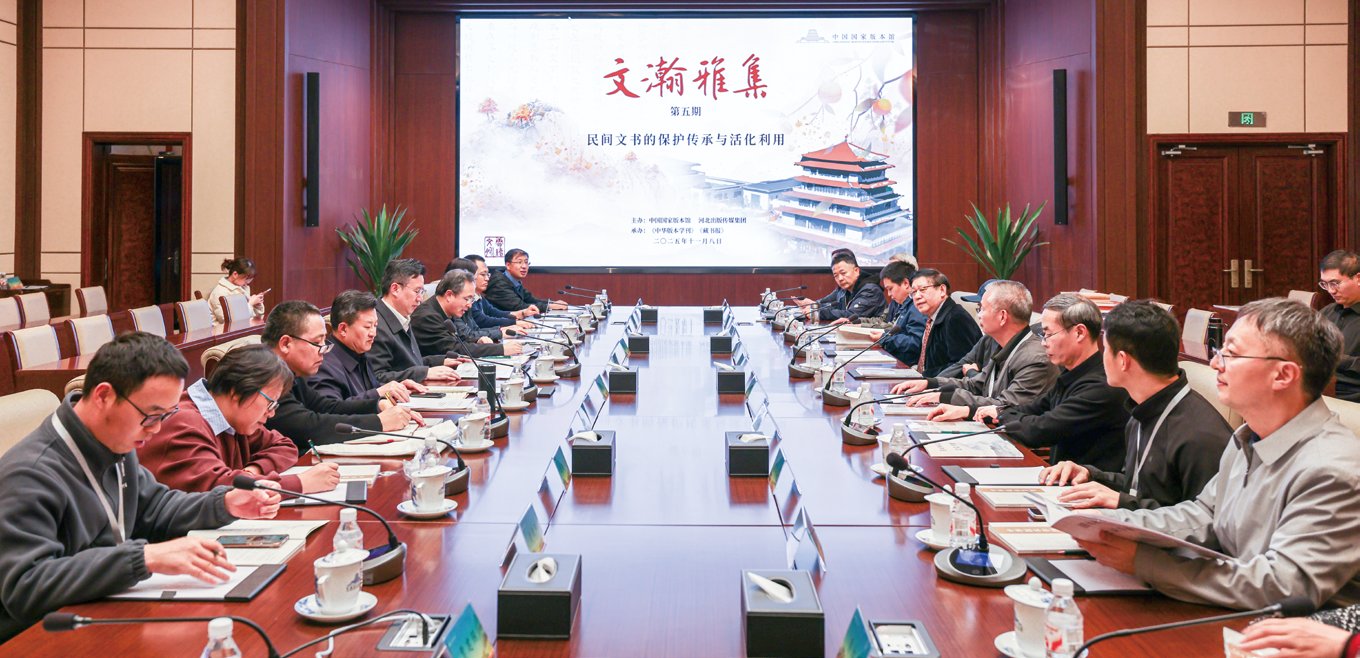左一为刘敦愿先生,右一为张维华先生
先严(刘敦愿)乃一介教席,平生悉以课徒为业,奉职山大学府五十载,教书一丝不苟,术业精益求精,桃李天下,功业有成,以文献功底深厚和治学态度严谨之见长,自出机杼而别树一帜。先严於案牍劳形与埋首故纸之余,最大爱好及乐趣,则是阅读《福尔摩斯》、《尼罗河惨案》等侦探或推理小说聊以自娱,犹如身临其境从中领略蛛丝马迹之破案线索与缜密环节,对解惑历史之存疑深受启迪和助益。身为考古之人,先严早年致力於田野调查,在“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之教涯生中,令人难以忘怀之经历,首推其凭借一张清人古画而发现一处龙山文化。
先严出身於美术专业,对中西绘画素来颇有关注。他以见微知著之慧眼,明察秋毫之洞悉,按图索骥之所求,穷原竟委之探索,历尽艰辛,最终寻觅到胶州“三里河遗址”。
重温轶事,饶有兴味,是故稍以赘言娓娓道之:
一九五八年,在青岛文管会诸多藏品展览之中,尚有一件灰色陶罐,器壁刻有山东丹青大师高凤翰(字西园,号南村,亦称南阜山人,扬州八怪之一,胶州人,1683年生,1748年卒)名曰“吸古得深味”之所赋诗句与题记,颇为耐人寻味。不过此件无殊,平朴如常,其生成年代为之甚晚,陶器小口、圆肩和深腹之造型,迥非龙山之物。但无独有偶,事既凑巧,师长张维华先生(山东大学教授,著名秦汉史、明清史和中外交通史大家)於青岛文物店亦购一副高凤翰之水墨花卉(后捐赠山大历史系),画上也有相同题诗与记事,仅文字与其大同小异,尚无年月记载。即抄如下:
介子城边老瓦窑,田夫掘出说前朝;阿翁拾来插瓶供,常结莲房碗大绕。
余家介子城下,常得瓦器如罂罐,可充瓶供,插莲花,房大如碗,饱绽坚实,以其气足,生物可成也。
南阜老人左手画并志。
解析字里行间之玄机,探究图文并茂之奥秘。打开画卷,不觉一震,先严凝神谛视而爱不释手。此画格外注目之处,则是其中插有莲花和莲房的陶器与上述形制大相径庭,它是一款上有“流”和“鋬”,下有“三足”之器物,显然是件典型龙山文化之“陶鬶”,虽经画家写意夸张,但百变不离其宗,时代之特征仍是尤为明显。从而说明远在二百余年以前,龙山文化遗物业已被人所发现。
一九五九年,先严从青岛专程赶往济南(迁校之前,山东大学原址则在现今青岛海洋大学),执持高氏大作登门拜访王献唐先生(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金石学家以及版本学家),借重高才请其一辩真伪,细经甄别高氏画中遗篇坠款,确系仿冒赝品,先严闻之,失望莫及。此画虽非真迹,并且不知凡几(王献唐先生於抗战之前,也曾购置了同样一副,经鉴定实乃伪品,后来因未加珍惜也就不明丢失了。诸如此类,不一其人)。然而,赝品是由真迹临摹而来,无论作品真伪如何,其“陶鬶”无疑皆为写实之作。仅鉴於此,高凤翰之所谓“介子城”,当属一处未被发现之龙山文化,这个推论极具参酌价值,但正确与否,尚须通过实地考察加以验证。
因此之故,一九六零年(此时,山大已迁至济南),先严携其同僚行装就道远赴胶州,作了一次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与采集。
“介子城”位於距县城西南三四里之遥的古城村。据县志记载,它曾为春秋时期的介国、汉代时期的介亭所在地。是岁还仅存部分清代高台和乾隆时期的破损碑记,原为胶州一处名胜,然时过境迁与沧桑巨变,洎今其遗迹早已荡然无存。翌日,先严於古城村的东南之隅,发现一段长约百米,高约两至三米之残垣断壁,墙基上仍留存若干洞穴,其中还参杂些许绳纹陶片和豆柄等物,证明故城遗址的确存在,但是否归属春秋时代之介国,却难於辨别,既非此行目的,姑且兹不具论。虽经再三寻找,始终收获无几,除在村南临河断崖之处找到零星碎片之外,并未发现任何龙山遗物及其文化地层。由是以观,此地绝非高氏所云“瓦器如罂罐”出土之处。倘若如此,其“陶鬶”究竟从何而来?先严莫测其由而陷入沉思默想。高凤翰题记之“余家介子城下”者,乃就大体范畴而言,高氏以古地为说,想必是增强其艺术创作之诗情画意罢了。所存疑虑,涣然冰释。先严继而推测高氏“陶鬶”及其“老瓦窑”,肯定离此相距不远。若然,但凡再进一步,跟踪追击,其未解之谜行将告破而计日程功。於是先严电迈高氏故里———“南三里河村”(此处有条贯穿东西流域之河,称为“三里河”,南北两村皆因其故得名而来)。行径乡间,询於刍荛。据当地老农告知,村边周围时有铜器、陶器以及诸多瓦砾出土。先严循其所指前趋一探虚实,或许是其语焉不详,使之巡察徒劳而不尽人意。先严再谋计议而另行他往,苦逾三日,功不唐捐,先严沿河两岸屡经搜寻,却在“北三里河村”附近(仅与高氏家乡隔河相望。其范围:东西约二百米,南北约三百米。纵横村道将其分割成大小不一四个部分,面积孔大且地表多有遗物暴露),陆续发现了几处灰坑与大量的残缺鬶片。尔后,又接连采集到某些石器(其中有件较为完整的“石锛”,则是先严用所剩半包香烟与老乡交换得来),将其纤悉无遗予以罗缕纪存,按序依次编号、测绘、粘接和修复。先严负任蒙劳与时积日累,使之初露端倪而渐入佳境,曙光在望,不日或将方见分晓。但孰事难料,恰待拍照及存档之际,徒因房东两小顽童与家犬互逐嬉戏,不慎将其复原标本打翻在地而毁于一旦,旷日所费心血随即亦付东流,乃至先严锐挫望绝,殊有不堪愁绪於言外。何奈,此行刻期已至,半途之业只得暂尔搁浅。先严遗憾回府,以待再图来兹。
返济过后,先严百虑攒心而自顾不暇。在许久操劳与起居的无律之中,饮食不周和营养不良,故使康泰受损,躯躬抱恙,疾患时作时止,最终导致其“胃穿孔”病发而紧急送医抢救,结果切除了大半个胃。性命虽保,但元气大伤,从此“十二指肠溃疡”就一直伴随终身。区区困苦,岂能甘休?成败利钝在此一举,先严不迪医嘱安心静养,却依仍旧贯而夙兴夜寐,目不交睫而挑灯夜战。不宁唯是,他还励策老少家人竭力投入其中,以责为重,以舍为营,煞费周章重将诸此破陶碎瓦加以俢补与整合(寒舍混乱似狼藉,犹同废品收购站)。
综观胶州调查之所集文物,通过其时代和类型与异地相互参照及反复比对,咸与日照“两城镇遗址”(典型特征:流部较为宽短,前肢二足稍短,后肢一足肥壮,其足端作实心锥状)等量齐观。比较和审视彼此关系遥相呼应之近似与吻合,足以证明两者文化来龙去脉之异曲和同工,不仅是“源远流长”,并且是“同宗一脉”。若以溯流觅源为伊始,势以归根结底而告终。故此断定,高氏笔下之“陶鬶”由此出土,必是彰明较著而毋庸置疑。至幸,至幸!旗开称捷,深庆五衷,先严等人不胜激动之情溢於言表。父云今犹在耳:“天不我欺”,又曰:“微愿可偿也”。何曾料想,言之所预果如其然,高氏所谓“老瓦窑”之地,原来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之龙山文化———胶州“三里河遗址”(距今已有4300多年之历史)。事已至此,卒底於成,其史前文明之神秘面纱终被揭开。
高凤翰之画为先严锲而不舍之发现,提供了重要之线索;而先严按图索骥之验证,又为日后考古发掘奠定了坚实之基础(1974年和1975年,经由中国科学院山东考古所接连两次大规模的现场发掘,确定该遗址为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上下叠加,共有2000余件文物出土;1996年和2006年先后被列为山东省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於此同时,反过来也验证了高氏遗作所记载之真实性,故而将龙山文化遗物发现之时限大为提前,因此极大丰富和提高了龙山文化之研究史料与历史价值。
先严黾勉从事,不敢告劳。一生忙碌,四处奔波,敬业之心使其足遍齐鲁各地而乐此不疲。某次野外调查归来,喜逢幺儿降临,便欣然为之取名“陶陶”。弄璋之喜而名之以瓦,与其说是“纪念”不如说是“明志”更谓切宜,可见先严对田野考古感情之深,自不待言。
岁月悠悠,人生几何,五十余春秋倏然即逝,慈父见背,墓木已拱。方今,追思先严之往昔,道念霜露之纪辰,谨以拙文述之而飨读者。此事虽小,微不足道,但在中国考古史上却乃趣谈佳话,倍感意犹未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