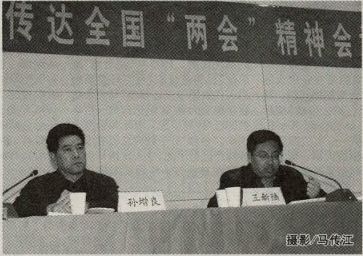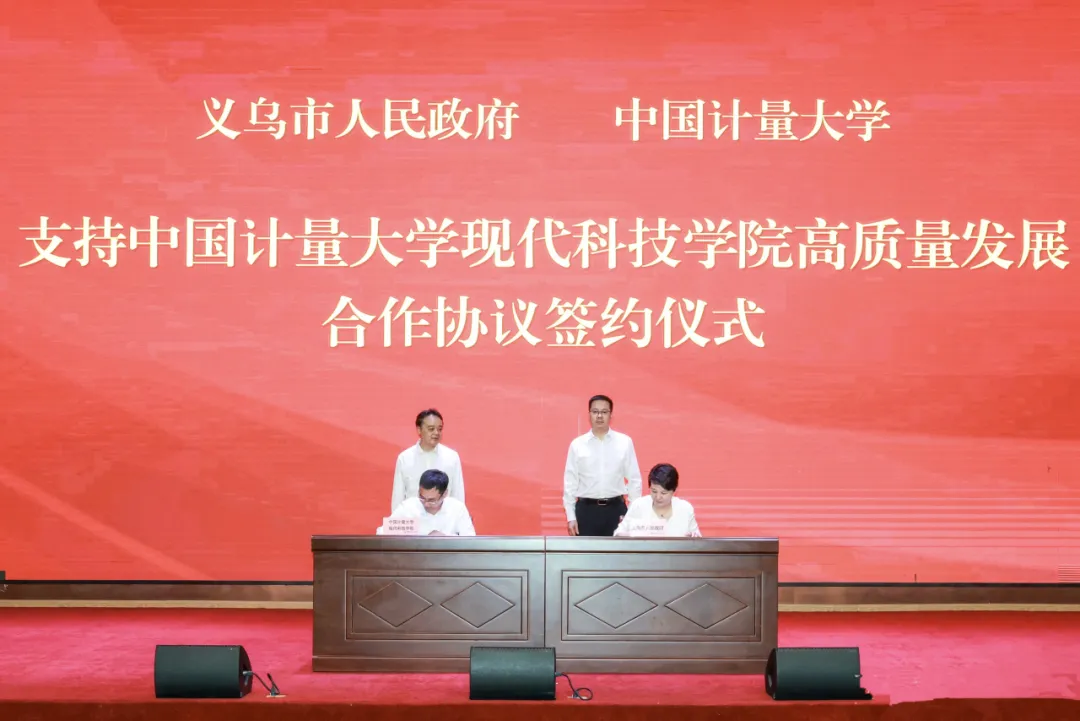文学 在漂泊中永———记“漂泊作家”曾哲的人文主义创作
曾哲,这个名字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也一样,某天图书馆书廊尽头的回眸刹那,我看到了这么一本书———《藏北草原,我的羊皮袄》。藏北,我喜欢的地方,草原,也是。
就是这么结识曾哲的。心灵的感应仅仅源于对同一地域同一种生活的向往。
在曾哲的一生中,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无论是他身上独有的漂泊者的气质,还是他那种不恃张扬、低调处世的人生哲学;他的文字质朴、干净让久陷低靡的消费文学中的人们品尝到一丝返璞归真的甘甜;而他在漂泊的驿站中的种种爱心,又不单单是义举所能解释的,这种爱心渗透着一种博爱、追求和谐的大气。
因迷惘而漂泊1989年,曾哲背井离乡,沿着西部边疆从内蒙古一直走到广西,西北西南十几个省,走了1年零2个月。用他的话说,第一次出外漂泊,是去治愈心理和精神的苦闷。当然随他一起流浪的还有他的文字。但是这一路上,写书的计划没有按计划进行。曾哲说:“看到生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写作的意义便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如果说一个作家能够忠实于自己的心灵的话,那么文学,即使是作为一件附属品,也会随之显得诚实。曾哲在漂泊中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出口,也将自己在漂泊中磨砺出的特有气质完整地融入了自己的文字。
《苗岭的夏天》是我接触到他的第一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曾哲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也给我意外的感动。
其中,写到在展芒寨,村长为招待公家人决定杀一头牛犊,阿江、阿阳却因为耐不住蚊虫的叮咬,而不顾村长苦苦挽留执意离去的时候,“我心里闷闷的加了些歉意”,作者的这种歉意,并不是为阿江、阿阳的轻视与无礼,而是内心深处对于自己的光临为展芒寨带来的难堪与尴尬,说到底,是作者对边地少数民族的人民、生活以及文化的关注与尊重。
这段描写同时也打消了一直以来困惑着我的疑虑。曾哲何德何能,赤裸裸啥家什不带,单凭一长肉块上面顶着个圆肉球,就穿越山涧谷底,走访20多个少数民族。凭啥?答案就两个字:真诚。
作者心理和精神苦闷的真正解脱或许就在这一次次真诚地交往中。作者把漂泊过程中的结识分离形容为走进走出,作者走进之前若是精神恍惚的话,那么走出之后,必是神采奕奕。漂泊伊始的种种困惑与迷惘就在一次次的走进走出中遗失了,心灵与文学在同一旅途中完成了自我实现。
最后的突围许多文人只能让我由衷地赞叹,却很难让我彻头彻尾的折服。曾哲,却是个例外。
曾哲某种意义上也是为文学而漂泊,但最后他却做出了远远高于文学的成就。随着他的思想境界以及思想质量的升华,他已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漂泊者,而是一个对民族的命运,对人民的生活非常上心的有责任感的中国作家。
在漂泊的驿站中,他留下了一粒粒文明的种子。利用自己的稿费,办起了独龙江的第一所小学,并义务教学达半年之久。几年之后,在祖国的西部边疆帕米尔高原,曾哲携带着清华紫光人的寄托,建成了属于这儿的第一所正规小学。
如果说,所有的路都有起点与终点,我相信,1989年的漂泊是曾哲的起点,而他真正找到方向则是在他办起第一所小学之后,至于终点,则遥遥无期。
我想,今后如果非要找一个理由来记住曾哲,我选择的不仅仅是他的文字,如果只有一种选择,更不会是他的文字。
文学,在漂泊中永恒假如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需要还乡的话,那么小说会继续漂泊吗?这是曾哲的疑问,我想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人有终,小说却没有终点,身体会累,心灵不会,况且,漂泊久了的人最富有的是记忆,这就足够小说再次漂泊的了。
我想历史不会因一个人的低调而将他忽略,尤其是在文学这条大河中,清洁的一股定不会为明眼人所遗漏,毕竟,我们掬的就是这一捧。
曾哲,北京人,著名作家,近年来主要从事漂泊文学的创作与实践。已出版的作品有:诗集《远去的天》,长篇漂泊小说《呼吸明天》,长篇漂泊笔记《离别北京的天》、《西路无碑》、《徒步,加德满都到拉萨》等。曾获第二届、第三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