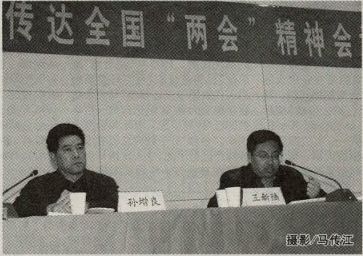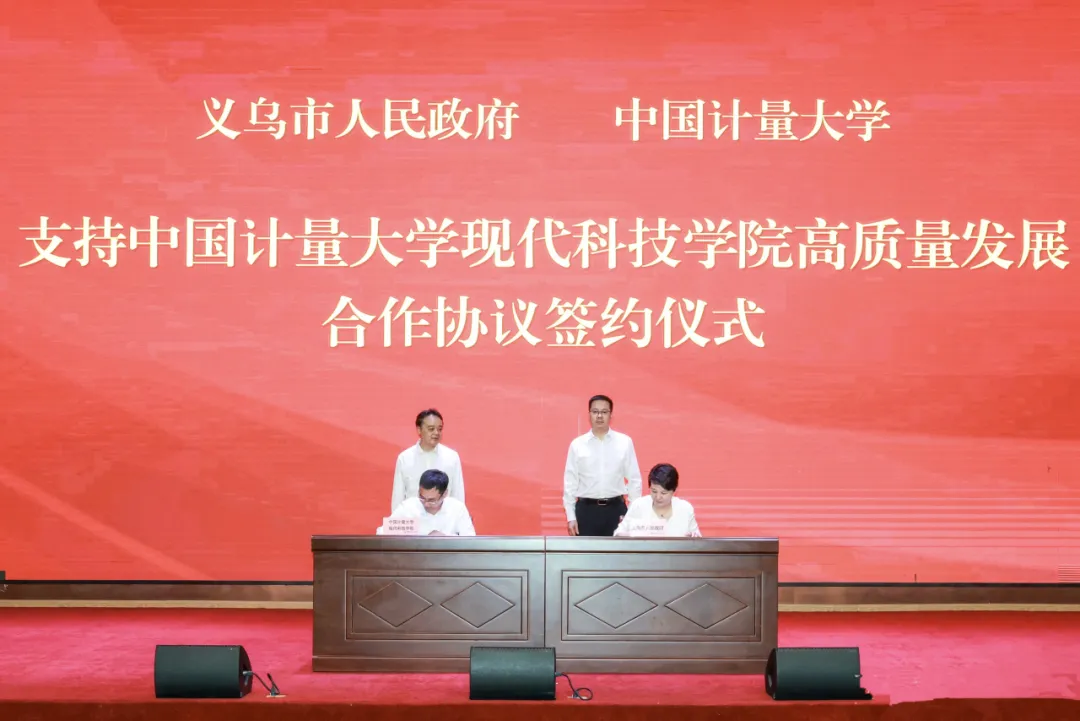关于鲁迅的闲话04级中文系 徐广舟
读懂鲁迅是难的。有一种说法认为要读懂鲁迅必须等到30岁以后 ,这种说法有点偏颇,但大体上是没错的。很难设想没有经历过生活苦难敲打、对生活没感觉的人会对鲁迅感兴趣。因为鲁迅的眼光太毒辣、智慧太突出,从而渗透了生活的阴暗本质,其内心充满太过深重的绝望。
我喜欢鲁迅这个人,是从阅读他的散文作品开始的。在鲁迅的文体中,我喜欢的是他的散文,很容易与那些童稚的乐趣和鲜活的描写产生共鸣,可以一口气读很多篇。我最喜欢的是他的《野草》,每一次阅读都是新的,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拜读,因为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根本无法平视它,而且我大都是在苦闷的时候阅读的,心常常在那些貌似阴冷的文字中得到温暖。
很少有人会给我这种多重感受:不喜欢、不太喜欢、喜欢、很喜欢。作为一个人,鲁迅是丰富的、经得起品味的。我喜欢!
我是学中文的,平时喜欢写点东西,但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写作,我都还没入门,只是把文学作为功课来做,把写作当作消遣———与别人玩电脑游戏或打篮球的性质是一样的。因此,不敢妄谈对文学或对哪位作家有研究,对鲁迅更是不敢胡扯,不像有的人那样,说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绝交是“莫名其妙”,时间过去那么长了,谁也无法重现当时的具体情况,前人留下的记录材料是否可靠还说不清楚,更别说由此演绎出来的所谓“见解”了,但是,鲁迅和胡适之间的纠葛真的莫名其妙么?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至少在鲁迅自己看来,他和胡适不是一路人。用“莫名其妙”来搪塞学术是不负责的,对两位先人来说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中文系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由于将‘学习和研究中文’当作谋生的职业,反而逐渐失去了作为文学的许多东西。”钱理群的话,我深以为然。古人云:“游于艺”。文学作为艺术来研究时离不开高深的学理,但也不能太过刻板,否则,就容易被它束缚。
我对鲁迅感兴趣,还因为他文字中强烈的现世情怀,他对国民特别是农民劣根性的挖掘和对农民那种矛盾的情感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深深地激荡着我的灵魂,使我对我的父辈及我自身的认识超越了小农意识———对父辈既体谅和理解,又审慎地批判。所以,那种对农民盲目赞美或者过分鄙视的批判都无法取得我的认同。我的基本立场是我是农民的儿子(一个乡下人、一个农民),有能力的话要为农民代言,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偏激地否定自己的出身,否则,就是忘本;另一方面,更要警惕农民自身的局限,批判他们朴实的外表下掩盖的人之恶性,只有比他们站得高些才有帮助他们寻求自我突破之路的可能性。而这些都是和当下人紧密相连的命题———过去是如此将来也这样。
钱理群先生说:“对鲁迅来说,‘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是他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同时也是他的价值尺度。”
对鲁迅的研究也应该像鲁迅研究生活那样,紧密地贴近生活,把矛头或曰视角指向当下生活,提出鲜活的个人见解甚至建设性的思维方式,给人们提供可以参阅的独特体验或经验。只有这样,鲁迅研究才不会仅仅作为一种生存手段。
社会进步的背后存在着知识工具化的悲哀。去年在新浪网上看到过这样一则信息,说武汉地区的女大学生从事色情行业的占百分之十之多,其中中文、艺术、师范、外语等专业比例更高,而且“业内人士”很理直气壮地说这个门路和其它门路相比很合算。面对这种现象应该怎么办呢?鲁迅地下有知的话恐怕要被气活。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我们回避不了,这不是只靠阴阳怪气地说几句讽刺的话就能解决的。所以,一种别样的文化必须被建设,我们必须反思人除了物质需求究竟还需要什么,这种别样的文化包括哪些因子才合理?
有人说先进文化的方向就是鲁迅的方向,我们权且同意这种说法,那么,鲁迅研究的方式必须变革,不能只满足于对他生平经历的考证,这种替别人再活一次的事可以做,但最终目的指归一定是对现实生活有意义。否则,只是像李亚伟在《中文系》中写的那样,“能读懂《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恐天下笑耳!
挖掘鲁迅的当代性或许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挖掘鲁迅的当代性势在必行!
我在祈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