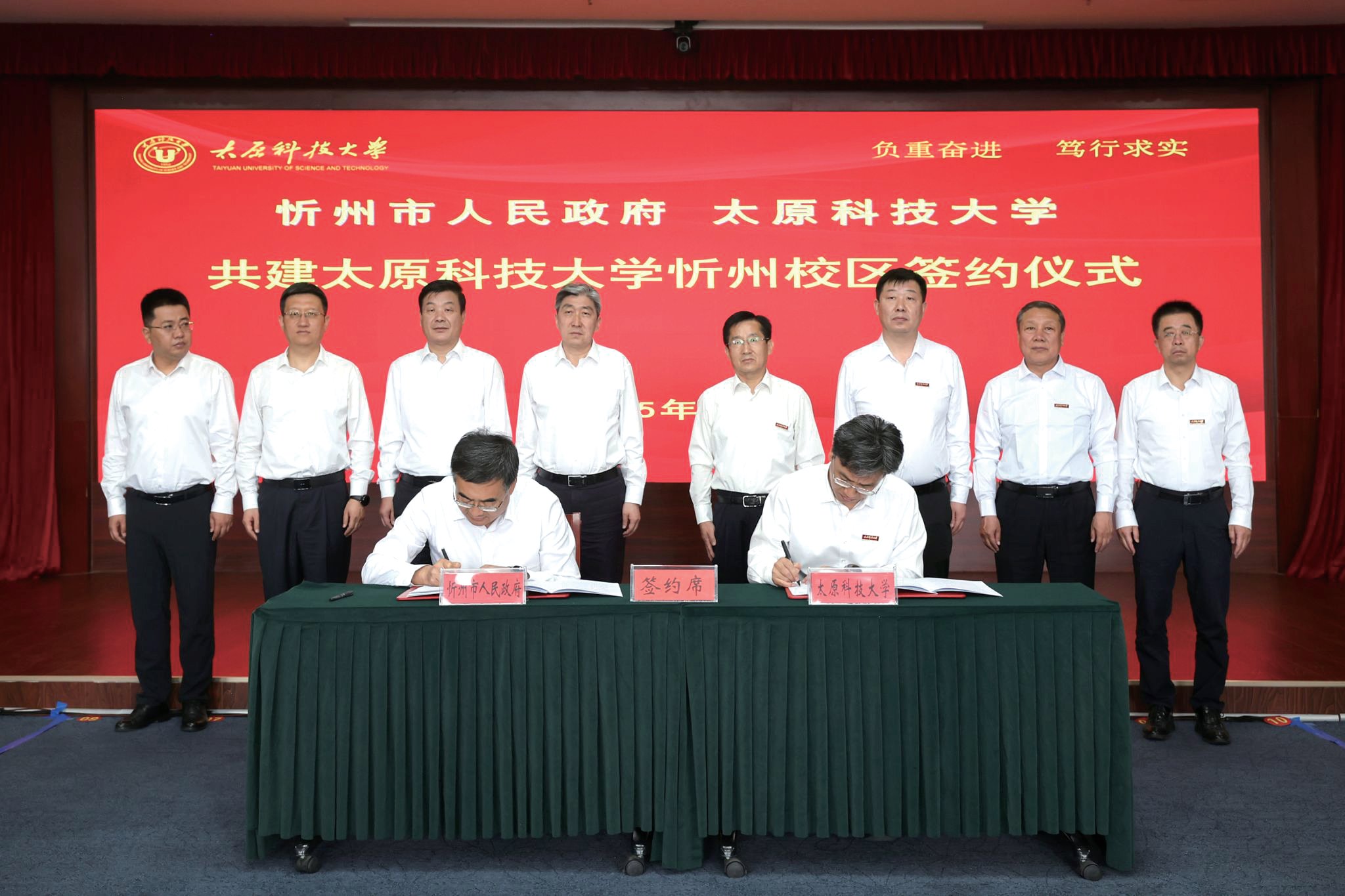从“对镜贴花黄”的花木兰到“淑女班”
在最近一次课堂上,对社会上出现的男女性别角色异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对做“女强人”或者“淑女”的价值选择的话题更是唇枪舌剑、争论激烈。由于文科女生居多,显然是主流话语,把男学生“呛得够狠”,视为“缺乏责任感、不努力拼搏、奋进”之人。笔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花木兰的主要审美取向、价值取向是做“女英雄”,还是做“淑女”?结果答案各异。大家几乎完整地将《木兰诗》背诵了一遍,可见花木兰的女英雄形象光耀千古、深入人心。
笔者有感而发,对花木兰的艺术形象及她的主要审美取向、价值取向进行了赏析。《木兰诗》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花木兰生于战乱频繁、民生多艰的北朝。她原本是个生活于劳动者家中平凡的闺阁女子。她擅长织布,勤劳善良,是战争破坏了她平静的生活。当战争来临,父老弟幼无力出征,花木兰“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她转战万里,奋勇杀敌,“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凯旋归来,战功卓著不受封赏,只愿回归久别的故乡。“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户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可以看出花木兰形象中的性别取向是女性而不是男性,也不是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其审美主要取向是女性之优美、女儿之柔美,虽然在战场上表现出勇敢英武的一面,但是她梦寐以求、迫不及待的是“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户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其主要价值取向是作陪伴父母的贤淑温柔之女,而不是“尚书郎”。整首诗描写战争的仅有6句,30个字。全诗紧扣“木兰是女郎”这一人物特点和审美取向来进行剪裁、描写,其中数句“不闻爷娘唤女声”那从征女儿思念父母、家乡的柔情感人至深。诗歌繁简得当,凡精雕细刻、浓墨重彩之笔都是在刻画花木兰的女性特征和女儿心理。正因为《木兰诗》塑造了一个女性特征鲜明的、贤淑善良、优美柔情而又勇敢英武的巾帼英雄形象,才得以流传千古、脍炙人口。如果花木兰没有“淑女”之美,仅有勇士之美,便不是花木兰;如果花木兰没有女儿似水柔情,仅有阳刚之气,更不是花木兰。
可见,“淑女”既是中华民族对女性内在美的最高审美标准,又是千百年来对女性评价的主要价值判断标准。《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这首民歌就是对“窈窕淑女”的歌颂赞美,自此为中华民族确立了女性美的典范;汉代乐府民歌《陌上桑》中描写了美丽绝伦、勤劳机智的“淑女”罗敷形象;从蔡文姬到李清照无不是 “淑女”与才女的完美统一。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淑女”便与封建意识的“三从四德”、“贞节牌坊”联系在一起,被批倒批臭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女性美的审美观发生了“革命性”巨变,那种敢于造反,搞阶级斗争的女性才美。对外开放后,国门打开,一会儿“西风”、一会儿“日流”、一会儿“韩潮”、一会儿“港星”,使不少青年男女迷失了自我。有的男孩子走路像 “风摆柳”,站着像“S”,伸手“兰花指”,说话“嗲声嗲气”;有的女孩子走路像“打夯”,说话像“打雷”,举手打人像“敲木鱼”,穿衣服布料节约得不能再节约……男女异化现象十分严重。
从原始社会开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女逐步有了分工。男性打猎、捕捞、征战,担负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国原始社会神话传说中的 《夸父逐日》、《羿射九日》、《鲧禹治水》等,都是男性社会角色的真实写照。他们敢于担当劳动重任、社会责任。到了阶级社会,男性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还是在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做出贡献、付诸牺牲都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西方推崇男性的“绅士风度”,举止优雅得体,尊重女性,生死关头把生的希望留给妇女、儿童和老人。社会主义社会提倡男女平等,绝对不是提倡男性女性化、男性中性化,绝对不是容忍男性不敢负责、不敢承担的懦弱无能。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强不息”、阳刚英武之男,民族便会衰亡;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保卫祖国、智勇血战之男,国家必然灭亡;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阳刚之美的男子,这个社会就会失去活力,逐步褪化;如果一个集体没有敢于创新、勇于拼搏之男,集体必然衰退甚至崩溃;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奋发向上、敢担责任之男,家庭便无底气和生机。
因此,笔者支持学校创建的“铁人班”,即便成不了“铁人”,也会熏陶出不但掌握专业文化知识,而且有阳刚之气、英雄气概、不抛弃、不放弃的男性。(包括意志坚定、坚忍不拔的女性。)从告别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女性就逐步从事养殖、纺织、刺绣等。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重男轻女、压迫妇女的现象便长期存在。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无产阶级解放,更没有人类的解放。我们为男女平等而奋斗,是为了实现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解放,绝对不是女性男性化,女性中性化。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厚德载物”、勤劳善良之女,民族便会消亡;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众多赤诚奉献、博爱敦厚之母,国家必然战乱;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阴柔之美的女子,这个社会便会枯燥无味,成为病态的社会;如果一个集体显在或潜在地缺乏女性无私地关爱、细致入微地呵护,集体便无法维系;如果一个家庭没有贤淑温柔、心灵手巧之女,家庭便缺乏温情蜜意与和睦幸福。
因此,笔者支持学校创建的“淑女班”,即便难以培养出古典美的“淑女”,也会熏陶出不但掌握专业文化知识,掌握女性应具有的基本技艺,而且谈吐优雅、举止端庄,给人以优美、柔美的审美感受的女性。
从“对镜帖花黄”的“淑女”花木兰到学校创办的“淑女班”,中华民族的女性审美观在这里有着内在的传承性和逻辑关联。教育需要继承也需要创新,教育史上创办女子学校是创新,男女合校也是创新。学校创办“铁人班”是创新,创办“淑女班”也是创新,走一条培养人才的创新之路有何惧哉!
总比顺“西风”、逐“日流”、随“韩潮”、追“港星”要好……总比男女性别异化,社会生活不和谐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