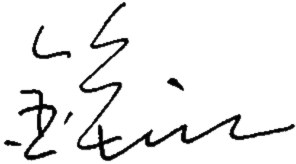刘宏球
一个稍显复杂的电影文本
《南京!南京!》的上映使今年以来有些沉寂的电影评论变得活跃而生动。或许,这已超越了对一部影片的讨论而成为一个小小的“文化现象”。一个稍显复杂的电影文本提供给我们多种解读的可能,本在情理之中。
陆川想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侵略者的屠杀和暴行、中国军人的反抗、中国普通家庭和个体的劫难、良知未泯的日本军人的反思与觉醒……应该说,他拍得很认真,战争场面的拍摄几乎可以和大片相媲美,而一些细节的表现又足以触动观众最敏感的神经;他用细腻的镜头刻画几个小人物的挣扎和反抗,也呈现出角川这一角色的心理世界。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上或许有更多的可圈可点之处:更能呈现历史感和中国黑暗岁月的黑白影调,同时发生在几处的大屠杀镜头的反复切换构成的平行蒙太奇,都在努力还原着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与“集体记忆”……直面自己,也直面对手,这需要勇气。他的镜头下的侵略者不再脸谱化,也没有把日本兵拍得如同小丑;他没有“美化”日本兵,而只是挖掘了角川未曾完全泯灭的良知。这个有些理想化的人物背后或许隐含着陆川对于这场战争更多的思考,也表达着在当今商业氛围浓烈的影视圈里他仍然保持着的艺术家的良心。
不过,陆川毕竟还显得年轻,对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把握还有些力不从心,他想告诉观众的思考太多、太杂,影片的叙事表现出一些断裂的痕迹,视点的设置更存在明显的疏漏。如果说影片是以角川的视角来呈现这一历史事件的话,那么全片应该是一个被限制的视角,他不应该看到他无法看到的场景,而片中发生在“范伟”家中的场景却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角川自杀以后的场景更成为没有来由的“讲述”。一部影片视角的转换并不奇怪,只是应该有很好的“缝合”,才不致于让人觉得转换的突兀。结尾的“大笑”尤其显得“没来由”,仅仅只是表现两个中国军人庆幸自己“活下来”吗?陆川似乎没有给我们更多的答案。
黄宝富
为什么要在我们的屈辱和疼痛上跳舞?
1937年的南京记忆,是我们多灾难的民族永难愈合的惨烈伤口和永难洗刷的种族屈辱。对于这充分呈现人性之恶的历史片段,电影工作者们一直努力将这不能更不该遗忘的悲惨段落影像化,国外电影人大多以直逼人心的纪录片形式,真实记录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和中国军民人间地狱的境遇,而陆川却用他所无力承担的反思想象力,编导了歧义丛生的《南京!南京!》,这是一部在我们民族的屈辱和疼痛上跳舞的商业电影。
第一,电影主题隐匿而暧昧。
审慎和严肃,是电影创作触及南京大屠杀这场灾难时必须遵循的态度,而显在的批判,更应是电影本体触目可及的思想线索。可是,陆川走得太远了。电影的三分之一,他努力还原守城士兵壮观的逃离、零星的抵抗和麻木地被屠杀;电影的三分之一,叙述拉贝神话及其破灭,中国妇女的被凌辱;电影的三分之一,表现日军肉体和精神的狂欢和所谓的人性反思。对中国军民被屠戮的同情和对日军禽兽本质的批判,是电影双线呈现的应该主题。可是,电影开始时士兵的逃亡和电影结尾时“小豆子”的笑、奔跑、吹蒲公英,混乱的开局和轻飘的结尾,“逃生和苟活”似乎成了电影的一种主题。尤其难以忍受,日军在“伤城”废墟上惊心动魄的舞蹈,杀人者,挥舞着杀人的手,在激越的鼓声中体现着他们的意志、祭奠着他们的亡灵,这应该是电影高潮的时间节点,却将电影镜头和精神力量给了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片尾,角川的自杀和伊田在河边水缸里的沐浴,一颗子弹和一缸水,无法承担30万亡灵的民族重量,这样矫饰的战争反思,苍白而无力,是非道德的甚至可以说是罪恶的。
第二,电影叙事散落而迷惘。
陆川以拉贝日记的复印页为电影叙述的形式框架,可是局部虚构和细节想象突破了拉贝可能的旁观视线,宏观叙事的野心和小叙述的追求,使影片真实情境的大绝望和悲惨性无法全面展开,因此电影缺乏将观众逐步推向愤怒、悲伤、仇恨的事件主线和情感节奏。影片结束在抒情的自然画面和生的愉悦之中,淡化和解构了历史存在的仇恨本质。叙事场域,没有标示南京的时空大全景,残垣和颓壁,难以确认这是“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的人类大灾难的发生地。
陆建雄、姜淑云、唐天祥、角川等众多叙述视点的断裂和游移,使影片难以结构统一起伏的情节脉络。陆建雄,作为中国士兵的男性视角,目睹和亲历南京城的失陷和大屠杀,因为自身被动的死亡,而让大屠杀的残酷场景逐渐退出;姜淑云,作为南京妇女被凌辱的女性视角,因为自身主动的死亡,完成了精神纯净的视点仪式;唐天祥,这个身负背叛者罪孽的人,视线不断地在敌我之间游动,说服力不强的成仁结果,也结束了影片着力刻画的灾难全景中的家庭描述;而角川,这被“誉为”“创新”的视角,矛盾和凌乱,他参与屠杀却不具备也没有全面的客观视野。叙事策略的乱,叙事视点的混,使电影的情绪线难以波浪式前进,最终形成负感情的高潮。
叙事细节的观点轻移和意识挪动,使我们曾经的伤痛更疼。寥寥几个日本士兵,集群的中国军民就举起了森林一样的手,然后是被缚,被杀戮;面对杀戮和强奸,陆川似乎更侧重后者事件细节的特写描述,为拯救兄弟姐妹的生命,一百名妇女流泪举起了她们的手,在敌人面前敞开了她们的身体,陆川更喜欢摧毁我们自尊的精神。陆川在导演思想中,再三强调,剧情中什么都可以删改,这场祭祀舞蹈不能动,让日军挥舞着充满神秘和力量的手,表现着他们的虔诚和齐心。我怀疑着,陆川的思想站位。
“南京!南京!”据说,是日军进攻南京之前的叫嚣和口令,陆川以此为题,他的思想倾向和视野位置,可想而知。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韩三平说,《南京!南京!》票房过亿,他就去裸奔;如果票房过1.5亿,陆川参与裸奔,这还是人话吗?面对我们民族的伤痛题材,他们首先想到的居然是金钱!
常立
“祭祀招魂”的镜头分析
卡夫卡很多年前说“电影使人们的眼睛千篇一律”,强调的是电影的强传播效果,德国名作《意志的胜利》能够使观众情不自禁地向纳粹(及其精神)致敬,陆川的《南京!南京!》中日军“祭祀招魂”一场戏也有着同样强大的传播效果,注定将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
陆川说,这场戏是为了表明战争的本质———胜利者的文化在失败者的文化的废墟上舞蹈,无疑有其现实批判和精神反思的意义。然而问题是,这场“文化的舞蹈”就其视听效果而言极具震撼力,视听语言也极尽庄重、铺陈、张扬之能事。意志薄弱的观众很可能如剧中“舞蹈者”一般被导向服从、服膺、驯服和屈服———即便如角川这等被虚构出的人道主义代表也在这一“精神舞蹈”中陷入魔障与迷狂。而我思考的是,是否有一种更好的电影叙事方法———既能表达陆川要表现的强势文化、精神控制和魔性嚣张、人性沦丧,又能给观众以审视和批判这一“舞蹈”的距离而非别无选择的顶礼膜拜?也许平行蒙太奇是可以试用的手法,在这场戏的适当之处插入几个业已表现过的南京屠城的悲惨镜头(音乐可以一直延续祭祀的音乐),既可以帮助观众从影像造成的精神催眠中离间出来,提醒观众这一胜利者的“舞蹈”是践踏在无数须臾不可忘的中国死难者的尸身和亡魂之上,又可以在叙事上为角川的自杀行为提供更充足的心理动机,它在视觉上表现为角川精神上的分裂———一方面被日本军国主义精神震慑、沉迷于菊与刀的日本文化,一方面被屠杀无辜者的现实刺激、被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拷问,人性分裂是比人性沦丧更充足的崩溃自杀的理由,毕竟人性沦丧的人只会更残酷地表现出兽性。尽管角川大抵出自陆川个人一厢情愿的虚构,但虚构还可以、也应该显得更真实一些。
尚再清
角川之死:一个苍白的注脚
这是我在师大看电影以来经历的最安静的一次退场。每个人都在经历一场思想的转变:以前我们只知道那些暴行是日本鬼子干的,现在我们发现,日本鬼子居然也是人。这种转变在电影上的体现并不始于《南京!南京!》,但由一个日本军官作为影片的主视角,《南京!南京!》在转变上的步子迈得相当大,也很需要勇气。可遗憾的是,陆川却停在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历经千难万苦,影片让即将赴死的角川说出了那句“活着比死了更艰难”的台词,然后就像完成了任务一样嘎然而止,仿佛在用一个人的死,为30万人的死做注脚,这是单薄苍白的;这个“人”和所有的“鬼子”格格不入,好像潜伏在魔鬼队伍里的天使,这是难以置信的。我们不那么愤怒了,甚至将同情给予了曾经痛恨的,但我们却茫然若失;我们依旧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能是“人”,又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了“鬼子”,怎么会变成“鬼子”……仇恨需要宣泄,历史需要反思,反思铭刻仇恨的历史,最容易吃力不讨好,但做好了就是杰作。《南京!南京!》很吃力,但离杰作还差一点。
王玲
南京,为陆川所装扮的南京
这是陆川通过影像所表达的,一个名叫角川的日本士兵活动在前台,贯穿于始终,对杀人有恐惧,对故乡有思念,甚至最后因对于屠杀的罪恶认识而放了两中国人后自杀,何其有人性。
然而,稍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在能找到的资料中,只有日兵自己拍下作为炫耀的,在满地尸骨中手提头骨开怀大笑的照片。日兵杀人比赛的报纸,从未有资料显示有日兵因愧疚而自杀,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如果因为屠杀中国人而自杀,那就是耻辱。即使有极少数,也无法代表日军的大部分。但影片中,这样一个有人性的日本人作为前景和近景出现,无疑就代表了这个民族,也代表了导演对于这个民族的看法。当角川释放了中国一老一少两士兵后,掏出枪来扣向自己的脑袋,并倒在阳春的土地上的时,仿佛代表了日本人对其罪行的忏悔。这个时候我们想,导演代替日本人认罪了,做了日本人那么多年来从不曾做过的事。
胡华燕
用温的眼光审视冷的战争
电影结束在角川解脱的枪声中,音乐舒缓,画面抒情,这与记忆中惨绝人寰的杀戮、纪念馆的累累白骨、愤怒的民族感情相去甚远。
然而,整部电影不乏类似的对日军充满人性的描绘:十几个日本兵在教堂看到上千中国人的恐慌;对姜淑云“shootme”的成全;射击唐天祥时的镜头处理;日本军官在慰安所如狼似虎的宣泄;日本士兵喊“我想回家”。表面看起来是对日军暴行的开脱,是在稀释仇恨,但实质上却加强了人类对战争的恐惧。
对于战争的参与者,不管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胜利方还是失败方都是种灾难和摧残。与在日本进行的次屠杀报复相比,我们更想看到的是和平。
国耻勿忘,30万同胞的血不会白流,然而,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腆着脸皮在全世界面前撒谎的国家,是应该“谈日色变”地处处嘘声处处骂,还是以博大胸怀的包容和自身实力的提高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我想,这部电影的成功不在于对历史的再现有多么的真实,而在于撬动了某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