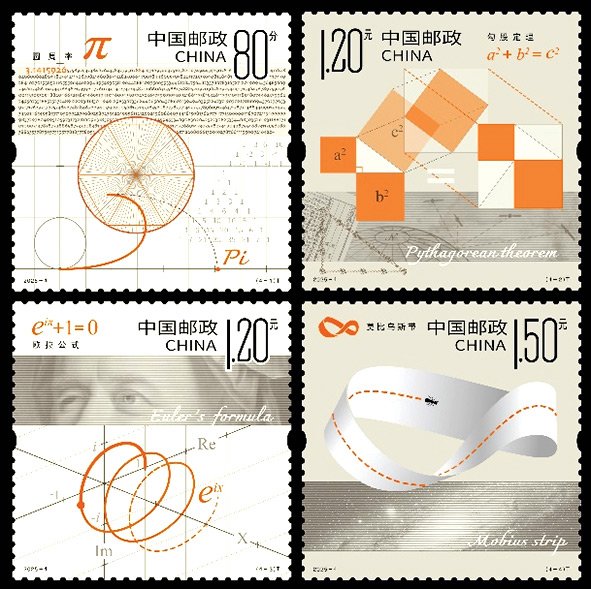阳春三月,风暖草薰。陌上花开,春意逼人。今年的清明节出人意料地艳阳高照,随处可见外出踏青扫墓、凭吊逝者的人们。在二十四节气中,清明是最具人生况味的一个节气。在春意盎然的时令,用一个节气提醒人们不忘对生命的感怀,强化慎终追远的人生意念,是我们的祖先理性务实生命观的体现。如今把清明节作为一个法定节日加以规定,正是与传统文化血脉舒张联结的有益举措。
现在清明祭扫的方式越发多元:几束鲜花、数样清供,简约静穆中寄寓着绵绵的哀思;衣着整洁、亲切地唱着圣歌,温婉的歌声和诵语呈现别种情致;依偎在一棵树旁,笑对一丛春花,默默倾诉着心中的思念,逝去的生命和自然是那么贴近;几炷燃香丝丝轻烟,纸钱焚化后纷飞飘散的灰片,古老而传统的祭奠方式,最能体现千年清明的悠久情韵;而新兴的网上凭吊哀祭方式,更是拓展了人们寄托情思的维度空间。
清明夜大雨骤然而降,选择夜读文本,自然要关联着和清明有关的生离死别这一关键词。我觉得,古往今来,死别的不可逆性,使得人们对死亡的惕怖态度始终没有多大的改变,而对于生离的情感牵挂则不然。当今便捷的交通缩小了生活的空间,通讯的发达抹去了时间的幅度,数千年来人们情感中特有的离情别绪所导致的愁苦哀伤,在现在似有逐渐麻木萎缩的趋势。也许在将来,人们有可能会无法理解、无法在情感上还原和逼近古诗文中比比皆是的离别情怀,品味不了离情别绪所蕴涵的爱恨情仇。于是,我选择了南朝文人江淹的 《别赋》作为清明夜读的文本。
把离别情作为唯一的咏叹内容,江淹的 《别赋》堪称典范。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开篇一声长叹,牵引出人生一幕幕的离别悲苦。无论是别魂飞扬的游子、龙马银鞍的贵戚,还是割慈忍爱的剑客、负羽从军的征人,或是一赴绝国的使者、结绶千里的仕宦,都摆脱不了离梦寂寞、怨怼伤神的离别情境。在人类丰富的情感中,离情别恨是一种对应互生的情绪,闺中与陌上、边塞和乡关、天涯与故土、庙堂和江湖……不论男女长幼,不分贵贱尊卑,情同此心,概莫能外,可谓是 “别虽一绪,事乃万族”。无论何时何地何人,离别情总是随空间的远近而伸缩,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随时令的变换而莫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从 《诗经》开始,人们就把春天定格为离别的固定场景,到了 《别赋》仍然在强化着这一情感定式: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之如何!”这特有的乐景衬哀的情景表现,在突显离别愁郁的同时又极具民族的审美意味。千百年来,空间造就了离情,时间镌刻着别绪, “有别必怨,有怨必盈”的别愁,此起彼伏、永不停歇地侵蚀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 “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离情,也就成为历代文人骚客摹写描画的永恒主题。“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 《别赋》收篇一问,回响千年,只是不知能否延绵不绝于将来?
谷雨前夕,去了一趟江苏兴化,陌上万亩垛田油菜花开令人流连忘返,同时踏访了郑板桥故居。感觉以往自己对郑板桥的认识极为肤浅,仅仅停留在 “扬州八怪”和 “难得糊涂”的流俗层面,对有 “三绝诗书画”美誉的郑板桥也是从俗于 “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良吏评价。从兴化归来,夜晨的一场大雨洗刷出一个阳光灿烂的谷雨日,在这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用了一天时间细细翻读了 《郑板桥集》。
板桥生前写刻了自己的 《家书》、《诗钞》、 《词钞》、 《小唱》和 《题画》,这些诗词文曲完整呈现了这位“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个性形象。他的诗文虽以 “放翁习气”自许,但又自信是当朝的 “清诗清文”。语言平实清朗,意兴疏雅淡定,既有 “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式的疏狂,也有 “历览名臣与佞臣,读书同慕古贤人;乌纱略戴心情变,黄阁旋登面目新”的理趣,更有 “雾裹山疑失,雷鸣雨未休;夕阳开一半,吐出望江楼”般的韵致。板桥诗句中巧用 “嫩”字前所未有: “更爱嫩晴天,寥寥三五笔”;“雨过天全嫩,楼新燕有情”; “御沟杨柳万千丝,雨过烟浓嫩日迟”等等,用语别致,令人耳目一新。板桥作词四十年,所谓 “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辛苏,老年淡忘学刘蒋”,在审美情致方面,洗却了花间遗韵,具有清词的雅致风格。如 《浪淘沙·烟寺晚钟》: “日落万山巅,一片云烟,位画坛怪杰书画艺术的感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