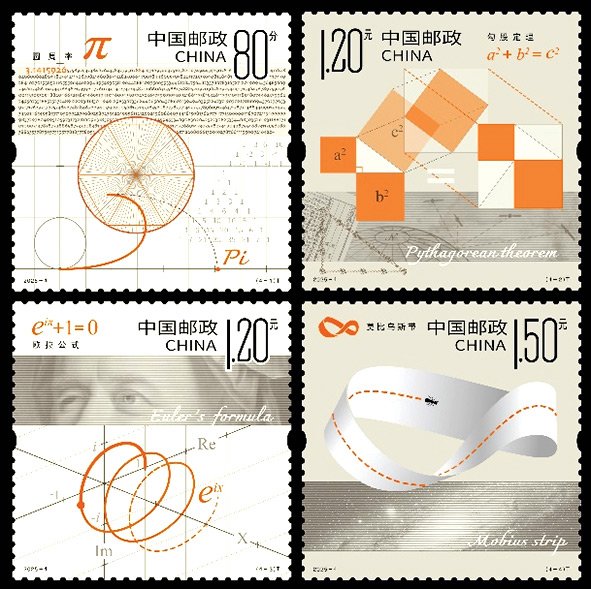■1992年与同学留影
英国的生态学会创建于1913年,美国的生态学会创建于1916年,其时正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现代科学起步比欧美迟得多,生态科学起步得更晚,而生态学会的建立则是晚上加晚了。然而中国迟到的生态学会却诞生在特殊背景里,一待成立就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1979年,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不久,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的新时期。那时也是全球环境恶化,世界面临五大社会问题———粮食、人口、资源、能量、环境———的重重困扰之时,当代生态科学的研究重点正在转向更加宏观、更加综合的生态系统研究方面。用句口号来表达,此时正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明天”时候。中国生态学会就是在这种光明与危机交织、挑战与机遇共存的形势下成立的。1979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在昆明市正式举行中国生态学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马世骏教授为生态学会首任理事长,我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负责生态学的教育和科普工作。
现在看来,20多年来中国广大干群对生态和环保重要性的认识能提高到今天水平,“科学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观念能如此深入人心,确实与一大批中国生态学家扎扎实实的教育研究,全心全意的奔走呼号是分不开的。自1979年中国生态学会成立那天起,生态学普及工作就没有停止过。我曾参与组织培训班15次,参加学习的骨干一千余人次。为青少年举办夏令营和知识竞赛6次,通过这些生态夏令营和生态学知识竞赛,青少年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生态学在“四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举办学习班来探讨初级、次级生产力研究方法问题,不过是一种无奈的补课之举。即使补课,也一定要补出成效来,多数主讲人按照要求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文字资料。我自己就与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祖望研究员一起写了《陆地生态系统次级生产力研究方法》,由学会事先油印好,上课时分发给学员们。由于做得和大学上课一样,比较正规,效果也就比较好。当年学习班的学员现在也分布在生态学的各条战线上,为保护生态环境做着各种努力,这尤为令人欣慰。
1987年11月在成都举行了中国生态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大会主题鲜明而响亮:“生态学与国民经济发展”。大会选举产生了由75人组成的第三届理事会,接着第一次理事会议选出了23名常务理事。理事会全票一致推选我担任理事长。
四年理事长任内,我首先对党政干部进行了普及生态学基础知识的教育。生态学会组织专家草拟了讲课提纲,经过在北京市委党校、河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校、顺义县委党校三次试讲,然后修改完善,终于形成了一本《生态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干部学习课本,于1989年由湖南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21.3万字,我撰写了四分之一的内容,并负责全书的统稿任务。这本书后来于1996年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而这次科普活动的意义绝非一个奖项所可涵盖,事实证明,一旦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认识和掌握了生态学基本理论知识,并在决策和管理中加以实践贯彻,就必然会减少许多短视和失误,也将会给社会带来福祉。我们的天空将会更加蔚蓝,我们的大地将会更加花红木翠、水清山碧。
第二项别有创意的工作,是调动全国各层次生态学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学术活动的活力。由于中国生态学会对各省市的生态学会,及中国生态学会属下的各学科专业委员会皆没有垂直领导关系,因此根据学会组织的特点,积极展开活动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组织召开了全国各省市生态学会秘书长工作会议,以“开展学术活动和提高学会活动能力”为议题。各级学会实际工作的班子是秘书处,秘书长的积极性调动了,学会的活力也就显示出来了。果然全国各省市学会秘书长会议一举行,思想明确了,各级学会积极性也就发挥出来,全国各地的学术活动便红红火火开展起来了。
在我担任理事长任内,有一件事让我痛悔不已,那就是我母亲于1984年逝世。
当时老父亲考虑我工作太忙,没及时把噩耗告诉我,待丧事办完才写信告诉我有关举丧的详情,这让我终身遗憾。20岁之前,母亲对我影响最大。父亲常年在上海经商,难得回家,家中里里外外撑持的就是母亲忙碌的身影。她克勤克俭,却让子女个个有机会上学;她教育子女决不取半分半厘不义之财,立身全凭奋斗进取。母亲的离世让我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悲痛中不能自拔。1989年6月,父亲也过世了。想起父亲一生侍奉祖母、养育儿女之不易,我心如刀割。想想自己,自1946年离宁波,1947年离上海来北京求学以来,几十年间奔波在外,很少回家看望父母,更别说在床前侍奉尽孝道了,心里觉得非常内疚。稍感宽慰的唯有自己在经济上对父母是尽了心力,挑了主要担子的。除去这一条,我深觉“不孝”,为两个老人实在做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