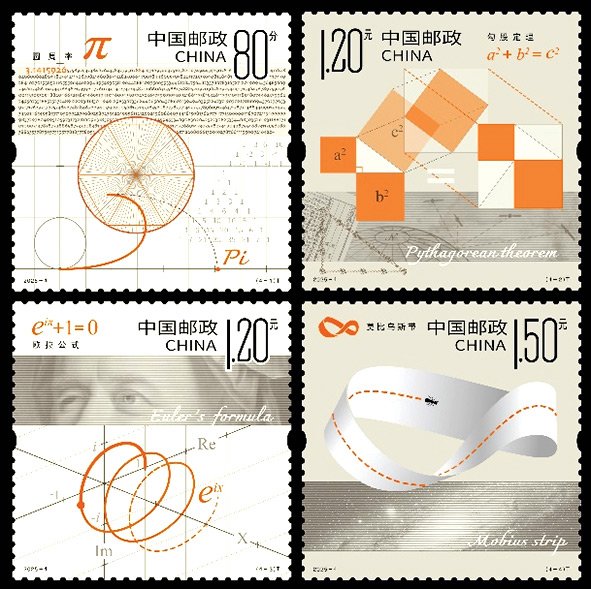我曾经惊叹于笔墨尽头传达的无穷意境,笔划之间,韵味十足,让你想到写字的人,他的性情,他的审美,甚至他的时代和他的经历。我曾经长久地徘徊在展出的书作前,没有人物和花草,只有墨迹的浓淡和线条,然而黑白颜色之间却呈现多姿多彩的意境,或古朴浑厚,或清丽婉约,或洒脱自如,或稚拙内秀。
小的时侯,见到爷爷拿着墨汁、毛笔和一本发黄的字帖(唐柳公权的《玄秘塔》),就被字帖上那骨清神隽、爽朗峻整的字体深深地吸引了。我经常跟着爷爷,在旁边看他写字,那一支粗大的斗笔,随着他手腕之间的轻重缓急、转侧变化,就呈现出或浓或淡的墨色,或粗或细的线条,或虚或实的结构,让幼小的我不由地感到兴奋和惊讶。虽然不懂书写的内容,但那种写字的韵味、运笔的快感却感染着我,令我心驰神往。
等到自己拿起毛笔后,才发现每一个汉字都是有生命的,有血有肉有骨有神有气。外在的是线条,用笔则如“力的激荡,气的流动,情的传递,生命的诉说”。线条不但可以给人以视觉的冲击,而且还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美妙的享受和持久的回味。因其蕴藏着密集的艺术含量,可以说得线条者得书法之半壁江山。因其象形,故书法“写”的就是事物的“简图”,或者说是以看得见的“相”来表现看不见的力。万毫齐发时或如漾轻波,或势如破竹,其变化无穷之处亦是精微美妙之所在。内在的则是风骨,字要凝重就必须让纸面承受更丰富的内容,诸如骨力、韧度、筋脉等,它们都是有重量有力度的,是实在的,而不是轻浮地一掠而过,顺山顺水。否则纵然运笔如风,点线如天马脱羁般驰骋,但笔迹若沉不下来则多外扬而少蕴蓄,经不起细品。
而要内外兼顾,结构章法则犹为重要。书法在结字上要求密处不犯、疏处不离,倚正向背、纵横呼应等,在紧守中宫、重心平稳的基础上极力追求斜侧变化,做到静中求动、动中求静,这样结字以求势美的规律与天地万物之理就通过意象思维的通路相连接了。在章法上讲求的“计白当黑”则是对空白的精心使用。空白所表现的空间意象不仅是为了烘托黑墨所表现的主体,而且还留有伸向宇宙空间的无限遐想。在古人擅长的意象思维里,空白包含着多层丰富的想象,以不写为写,从这一点上讲,由最纯粹而又最丰富的黑白两色来构成中国书法,也最能代表中华名族的传统思想。
书法除了追求形美、势美,更高层次的美则在于神韵之美,这是蕴涵在字里行间却又游离于实体之外的气韵,也是书家在心中、笔下、眼前所倾注深情的意境。这才是书法的内在灵魂,而现在的印刷体美则美矣,却失于性情。古往今来,一幅幅光照千秋的名家佳作之所以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就在于作品内含的书家的人格之美。“道美劲健,绝代无后”的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字里行间飘逸着晋代文人雅集“一觞一咏,畅叙幽情”的千古遗风。唐颜真卿满怀义愤写下的名作《祭侄文稿》,则畅达果断,自然天成,一泻千里,血泪淋漓。每读此稿,对正直敢言、老而弥坚,书品、人品冠世的颜真卿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宋苏东坡被贬黄州第三个年头书写的《寒食帖》中,但见随着感情的逐渐激越,用笔由平和逐渐沉着痛快,字形交替变化,率意奔放,书到后面,越发恣肆挥洒,最后,字形突然放大,突兀眼前,令人心惊胆战,一时他对处境的感慨、叹息,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心灵、性情、修养都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出来。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佳作迭出,书家通过对笔性的把握,对线质的锤炼,对结构的经营,对章法的巧构,尽情地演绎着性情之美、性灵之真。这些传世之作都是书家心灵的歌唱,灵魂的舞蹈,无不使人玩味终生而不厌,学其终生而不绝,读其终生而不释。
书法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学成的。多数人毕其一生之力也是只知皮毛,难以精进。而我也只是缘于爱好,一有闲暇,笔耕为乐,书写为快。虽难有所成,但总觉得学书法能静化身心,消除人生烦恼。写字需屏气凝神,一丝不苟,临摹古今书法名家的一笔一划,体味书写者的心境,感悟字的间架结构,品赏字的风格特点,从中理出自身的书写思路,每有所得,顿觉神清气爽,怡然自得,这时一切烦恼统统飞至九霄云外。书法还能陶冶情操,增强修养。言为心声,字为心影,古有心正则笔正之说,若平时不加强道德修养,没有高尚的思想境界,是难以写出佳品的,对于书法,我“在乎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当翰墨泄于笔端,流动于心腑之时,常因定心会意而忘记了自我。用心体味书法之美,必将受益终生。学海无涯,暂以笔舞墨浪心作舟来自渡,不亦乐乎!不自渡者,借他人之渡尤其是名人之渡,不亦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