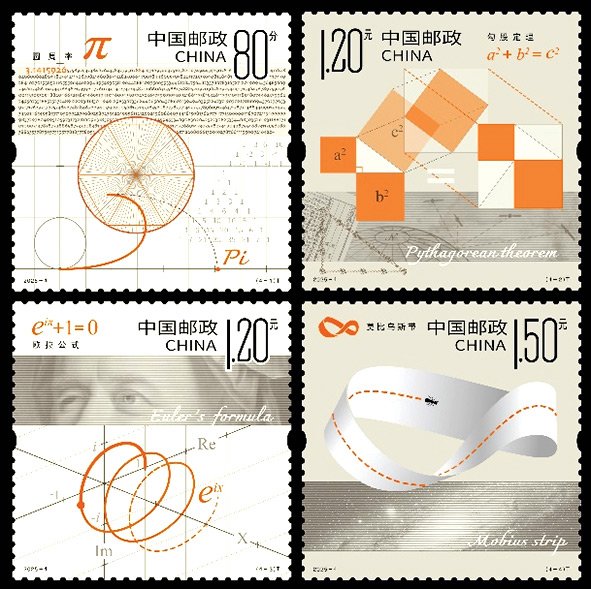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已是2009年的冬天,离着元旦、春节又越来越近了。已过而立之年的我,早已没有了对年节的那种渴望,代之的反而是对时光流逝、岁月蹉跎的一种感叹。不过,有一种味道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这一生都不会忘记,在记忆中象陈年的老酒一样,愈久而弥芳!———那让人沉醉的“年味”啊!
也许出生、成长在城市里的孩子们理解不了我们对春节的那种盼望和渴求,理解不了“70后”的我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些艰苦的日子里过年意味着什么。我出生在滨州近郊的农村,1979年底村子里随着国家实行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分了地,乡亲们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后,干劲十足。多年的自然灾害和不科学耕种早已把土地变得十分贫瘠,一年的粮食收成勉强能够养活一家人,尽管基本上都是玉米面饼子和窝头,不够时还要添补些地瓜干,但终于可以顿顿吃饱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已非常满足。至于新衣服、白面馒头、水饺、瓜子、糖块、鱼、肉……这些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在那时的农村,只有过年才穿得上、吃得到,要知道在当时市场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年代,庄稼人忙活一年,是攒不下多少钱的,只有到了年底,才能犒劳一下家人,当然也仅仅限于以上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日用品和食物。
我们这些刚刚上学的小孩可不管那么多,进了腊月就意味着要过年了,小男孩们缠着家里的大人在赶集时给买上几挂鞭炮,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就是小伙伴们的节日了。比一比谁家的鞭炮大、炸得响,那他就是我们的“首领”,天天跟着到处跑,把鞭炮插到人家的墙角里点响,随着屋子主人的呵斥一哄而散;抑或进行一场比赛,把鞭炮点着后扣在一个废旧小铁桶下,“轰”的一声,看谁的鞭炮把铁桶炸得高,一个不行、就放两个,记得最高的一次记录,是一个伙伴用他的鞭炮把铁桶炸飞到了房顶,大家欢呼雀跃……大人们只会在年前才肯恩赐那么几包鞭炮,伙伴们从来不会整包的去点,要把缠绕芯子的线解开,一个一个地每天数着放,不然,自己的放完了那就只有跟着跑、看别人放的份了。放学后,我们玩放鞭炮直到日头落西,家家房顶上的炊烟褪去,村里的街道上弥漫着柴草燃尽和粥饭的香味时,还在村落街道和田野上奔跑,对于正在成长阶段的小伙伴们来说,食物是诱人的,游戏却更诱人,只有听到家里母亲此起彼伏的一声声呼唤,才一个个地撒腿跑回,吃完了,看着母亲问:“娘,还有几天过年啊?”
到了腊月二十三,农历的“小年”,春节就真的要来了,小年后的日子,家家忙着打扫屋子、去除一年来的灰尘;准备年货,购买鱼啊、肉啊、鞭炮啊等等;还有,家里大人孩子都要置办一身新衣服,预备着过年穿啊!当然每家条件不同,购置的数量也不一样,但每样都是少不了的。再苦的人家,过年还是要隆重的,要拿出最好的衣服穿给别人看、拿最好的饭菜来招待亲朋,新的一年谁不愿有个新的开始呢?当时我家因为父亲在市里做工人,母亲是村里的民办代课老师,都有一份微薄但相对固定的收入,所以和村里其他家庭相比生活要好一些,年前家里置办的年货中多要买一些苹果之类的水果,能和一起玩耍的伙伴们享受苹果的美味也是当时很大的一种快乐。离年越近,感觉年的气味越浓厚,那是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其中既有空气中弥漫的年节食物的香味,还夹杂着盼望、兴奋时的一种感官上的感受,这种感觉会愈来愈强烈,直到春节的来临。初一早上,家家开始整包整包地放鞭炮,吃完饺子,然后大人带着孩子开始挨家挨户地给村里的长辈拜年,整个村子都沸腾起来,处在一种年的兴奋中,“年味”也在这一天达到高潮。接下来的初二、初三,大人们带着孩子走亲访友,去给自己或孩子的姥姥姥爷、舅舅、姑姑、姨们“磕头拜年”,亲戚们在这过年的几天里有说不完的话,感情也在这几天里得到了交流与升华。对于我们孩子们,重要的是和自己的表姐、表哥们玩得不亦乐乎!这种年味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孩子们在大街上比赛谁家的灯笼漂亮,有纸糊的、有竹篾编的、还有放上灯油的,各种各样,但提在手里都是一样的开心。十五过后,年味淡了,孩子们的心在家长的呵斥下又回到了书桌旁,要快点把寒假作业做完啊,不然要被老师罚的……日子又归于平静。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年的春节年味依然浓厚,尽管兴趣早已不再是那些鞭炮和瓜子,但感触很深的是过年的人们在衣食住行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及至我上高中时的1990年,村里的人们已不再为买多少肉而犯愁、孩子们也已不再是到过年时才能穿上新衣服,孩子们玩的鞭炮也不再是手工制作的“土鞭”,取而代之的是机器制作的鞭炮和“小沙炮”……处处感受到的是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巨大变化给乡亲们带来的巨大实惠,此时的人们不但过年吃得好、穿得好,而且平常一日三餐也都吃上了白面馒头,大人孩子都穿上了各式各样的漂亮衣服,自行车不再是村里那稀有的几辆“洋车”,已经在家庭普及,人们也都纷纷翻盖了新房,买上了黑白电视机,个别有些经济头脑、家庭条件好的甚至买上了彩电,人们纷纷向往着美好生活,村里的年轻小伙子、姑娘也忙着寻找出路、外出打工挣钱,感觉整个社会的人们都沉浸在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中之中!
我们家也在那时随着我和姐姐的高中求学而搬到城市,在随后的日子里,只在春节时才回到老家给长辈亲戚拜年,每当过年时都能同时感受到城市和农村的年味,总体的感觉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在逐渐变小。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人们都是一样的置办年货、一样热闹的过年,年货一样的丰富、年味一样的浓郁,吃饭、穿衣都已不再是人们的一种奢求,取而代之的是手机的普及和人们对汽车等高档消费品的追求。现在的我感受到的“年味”也早已不再夹杂小时候那种对吃、穿的渴望,更多的是一种对过年时与家人团聚、其乐融融感觉的陶醉与幸福。
也许对于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同龄人,或者“80后”,他们体会不到我们那种对年味的特殊感受,但在年节时,年味又如发酵成熟的老酒在鼻尖和脑窍中游走时,为这种感觉深深沉醉时,我有时在想,也许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年味”中吧!
(本文获我校《我与改革开放30年》征文评选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