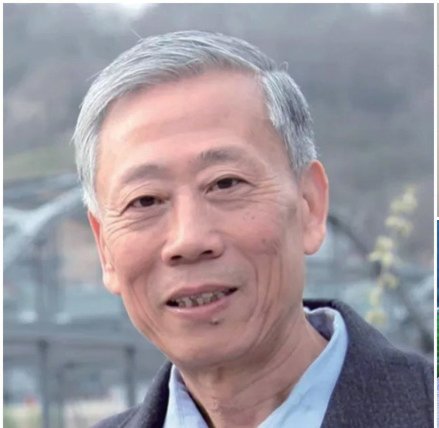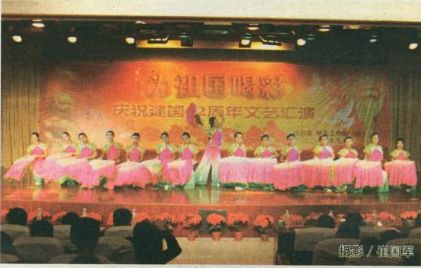孔子诗教观的诗意栖居在当年那座流动着的“仲尼学堂”里,以《诗经》的智慧考量人生,实际上也就是以人民的立场叩问苍凉的现实,以超越的智性安顿自我的身心。
2008年10月左右,网络蹿红歌曲《老鼠爱大米》有了一个“非常国学”的版本,就是《诗经》版的《鼠嗜米》:“吾闻君声,乃有异觉。辗转思之,毋敢相忘。君在我心,永难忘之。若当其日,诸愿皆偿。吾爱静女,上可鉴之。途远且艰,吾可誓之:吾爱静女,如鼠嗜米。风来雨打,永世同心。君在我心,纵苦纵难。惟愿君喜,九死无悔!”有人以为这是好事者“吃饱了饭撑着”。于我,则想起了《诗经》的“风雅颂”与“赋比兴”,更想起了孔子的“兴观群怨”与“思无邪”。
古人常说:“诗言志,歌咏言。”翘望那个极其久远的时代,人民在大地上深情地歌唱着,于是有了民歌;有心人把它们记录下来,于是有了《诗经》。《诗经》之体制有风、雅、颂三类,作法有赋、比、兴三种,它们也正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六义”。因其主要写照了黄河流域的民情和风物,《诗经》恰似一首宏大的“黄河谣”;因其侧重反映了周室东迁前后的世态和心态,《诗经》好比一部厚实的“周代史”。如果说《老鼠爱大米》是今天的“口水歌”,《诗经》又何尝不是当时的“梨花体”呢?
《诗经》之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孔子的编纂工作是功不可没的。《史记·孔子世家》有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汉书·艺文志》亦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从三千到三百,《诗经》的数量“少”了,但在人文上却“重”了起来。孔子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首开平民教育,《诗经》、《尚书》是其主干课程,他上课讲的是普通话而不是鲁国的方言,正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孔子的《诗经》教学同样卓有成效,因为那群可爱的学生已经能够运用往昔的民歌去思考当下的人生。在当年那座流动着的“仲尼学堂”里,以《诗经》的智慧考量人生,实际上也就是以人民的立场叩问苍凉的现实,以超越的智性安顿自我的身心。
子贡是孔门弟子中最富有的人,可谓儒商的鼻祖。据《论语·学而》记载,子贡曾经请教老师:“贫穷却不巴结奉承,有钱却不骄横自大,怎么样?”孔子答曰:“这么做固然很不错,但终究不如———虽然贫穷却乐于大道,纵使有钱却喜好礼义。”顿时,《诗经·卫风·淇奥》中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跃入了子贡的脑际,子贡觉得它就是老师所说的“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目睹《诗经》的精髓融进了子贡的内心,循循善诱的孔子鼓励道:“告诸往而知来者。你如此发挥,就能举一反三了。”
跟“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相比,“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确实更需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诗书”的人文如何开启“礼乐”的视界。且看《论语·八佾》的一段对话:子夏求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前两句出自《诗经·卫风·硕人》,第三句乃逸诗)的深意,孔子答之以“绘事后素”。“素以为绚兮”意即“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绘事后素”意即“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孔子之于《诗经》仿佛没有多说什么,但子夏却揣测到了 “绘事后素”的弦外之音正是 “礼后乎?”:礼乐也是生成于仁义之后,如同画花先得有白色的底子。
孔子曾对自己的儿子伯鱼说过:“如果不去慧心地体察《周南》、《召南》,一个人就会像正对着墙壁站立那样,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论语·阳货》)跟子贡、子夏讨论《诗经》时,孔子还说过同样一句话:“始可与言《诗》已矣。”只会记诵《诗经》还远远不够,更要心中盈溢着“诗之思”。惟其如此,三千弟子才可能尾随着孔子逼近《诗经》的堂奥:“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诗经》也是诗,诗之于人类而言是比《诗经》更为本真的一种存在境域,所以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在此没有给“诗”穿上书名号。“兴”之一字,乃“引譬连类”,乃 “感发意志”,盖因诗篇之能感动鼓舞;“观”之一字,乃“观风俗之盛衰”,乃“考见得失”,盖因诗篇之能观照现实;“群”之一字,乃“群居相切磋”,乃“和而不流”,盖因诗篇之能整合人心;“怨”之一字,乃“怨刺上政”,乃“怨而不怒”,盖因诗篇之能针砭时弊。“兴”是一种想像力,“观”是一种洞察力,“群”是一种凝聚力,“怨”是一种批判力,———只要拥有这些力量,广大的人民就能够超越“不道德”的社会,成就为一个“道德”的人!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无邪”典出《诗经·鲁颂·駉篇》,本是一个无义的语首词,但孔子却诠释为“思想纯正”。之于《诗经》,这是“断章取义”;之于人心,这又何尝不是“以意逆志”呢?“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思想纯正了方能诗意地栖居,真切的“温柔敦厚”正根源于“思无邪”,所以,于孔子的诗教观,“兴观群怨”旨在“涵盖乾坤”,“思无邪”则力图“截断众流”。只是一个“虚词”要在今天变得“充实”起来,依然有待于我们执著地践履那句箴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古往今来,诗意地栖居哪里是一件轻松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