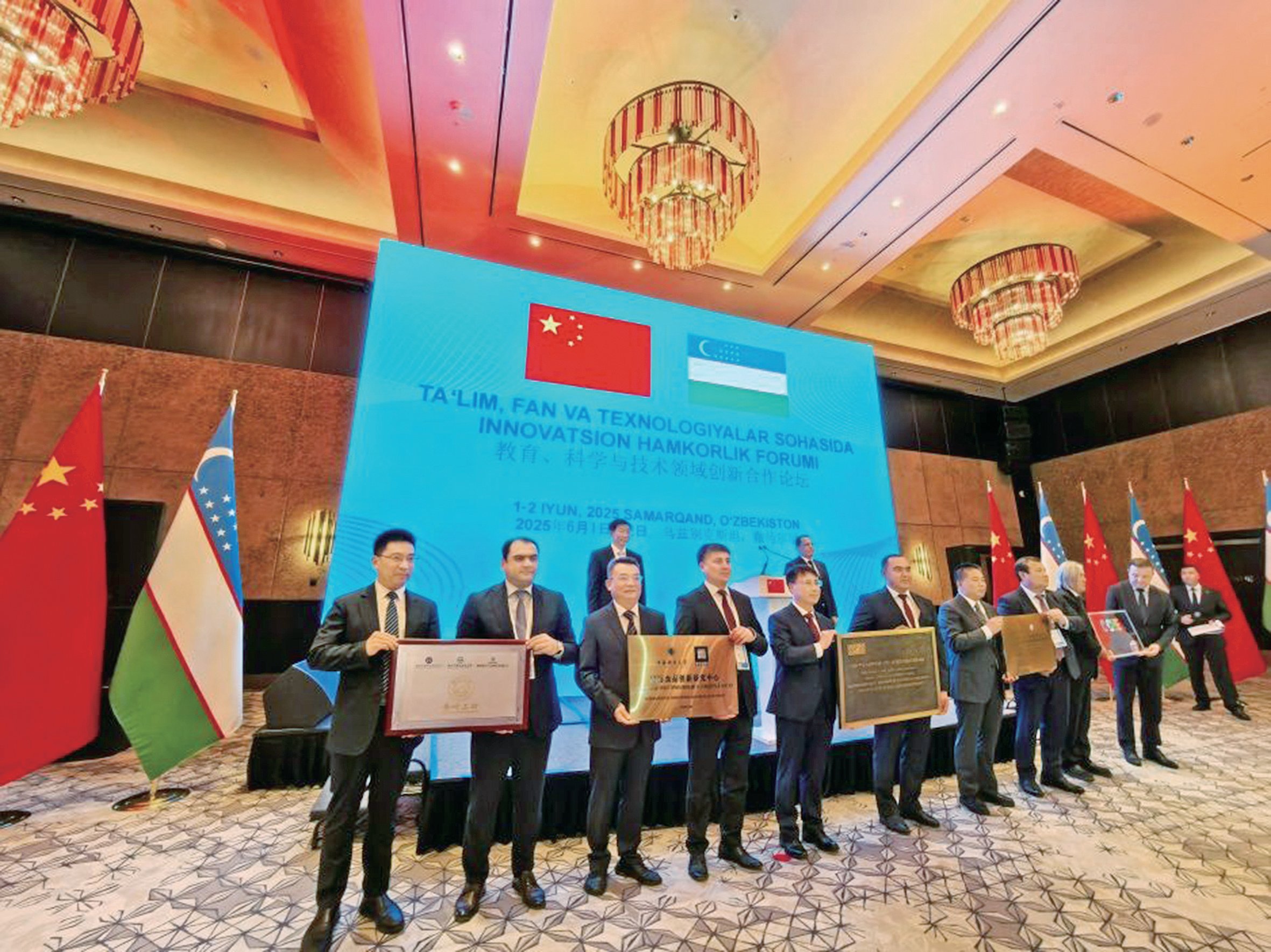“等待”的价值,既不在“等”,更不在“待”。
有人问《等待戈多》的作者“戈多”到底是谁,贝克特耸耸肩膀说道:“我要是知道‘戈多’是谁的话早就在文章中写出来了。”但即便不知道戈多真正是谁,那两个流浪汉还是在黄昏中的那棵枯树下死心塌地的等下去。他们一面做着闻臭靴子之类的无聊动作,一面在语无伦次的梦呓。当知道戈多又不来时,他们便打算以上吊的方式一死了之,结果却把裤带拉断了,于是只能毫无希望的等待下去。
《等待戈多》虽是一出荒诞剧,但却折射出了人类将诸多事情付诸于等待,最终希望却化为泡影的悲惨现实。无疑,有了人类便有了“等待”,可这“等待”并不是纯粹期待,而是一种生存状态,甚至是无奈至极的生存状态,它意味着人类生活中无休止的等待,却又不知道到底在等待什么,所以就永远不可能等来任何东西!
忘不了公元前三千五百年的那个夜晚:一场由男人发起的暴动终于推翻了“母系氏族”社会,并以充满暴力与血腥的“父系氏族”取而代之。但是,尽管女人失去了世界,世界却并不能失去女人。也似乎正是打那儿以后,“等待”一词便逐渐走向了成熟,并形成了一条“铁的定律”,即在“等待”的角色扮演中,女人一般都为主角,男人一般为配角。或许,在某个雁落平沙的荒漠有个征夫对着蜀道寒云悲叹:“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或许,在那个霞铺江上的川上有个倦客迎着魏水秋风低吟:“那年离别
日,只道住桐庐。桐
庐人不见,今得广州
书。”但,这又怎能与
“闺中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忽
见陌头杨柳色,悔教
夫婿觅封侯”、“夫戍
边关妾在吴,西风吹
妾妾忧夫。一行书信
千行泪,寒到君边衣
到无”、“美人如花隔
云端……天长路远
魂飞苦,梦魂不到关
山难。长相思,摧心
肝”的女性那般凄苦
的等待和期盼相提
并论?!况且,男人在
等待时起码还可以
点燃一支烟燃烧孤
独,而女人的等待却
往往只有从秋流到
冬、从春流到夏的泪
水迷糊欲穿的望眼。所以,从古至今,似乎也只有“望夫石”、“望江女”,却始终未听有“望妻石”、“望江郎”!所以,自古至今就有不少痴情女,但还有更多的薄情郎!
尽管我们常说离合总关情、聚散皆是缘,但当你看到寒衣做好送情郎的少妇那热切、兴奋而又不乏焦躁的眼神时,当你读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诗句时,当你听到小孟姜哭倒长城时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哭声时,你,只要良心未泯,都会经意不经意的不寒而栗。
林妹妹于无可奈何之年、百花凋零之月、数峰凄苦之日孑然一身:提锄挽篮、收一方落红,扶柳洒泪、送一池飘絮,但始终未能等到宝玉的归来。此后,微风依然抚过琴弦,落花依然飘在水上,但命运的尘埃却依然湮没了黄尘古道,时间的风霜也依然荒芜了烽火边城,同时,也使得那双葬花抚琴的素手香消玉殒、灰飞烟灭!
其实,无论宇宙洪荒也好,天地玄黄也罢,当他/她的地老天荒已经不再属于你时,与其像“等待戈多”那般遥遥无期地等待下去,不如就选择走吧!当生命的警钟一再告诉你:你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那么走吧!就让你那踏雪寻梅的足迹留在寒霜初降的板桥上。
其实,“等待”的价值,既不在“等”,也不在“待”,而是在你已经没有时间等待下去时能否做出“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