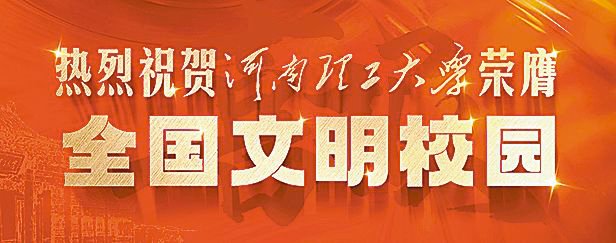上初中时,学校离家有12里之遥。那时公路没通,一条乡间大道,零散地铺了些石板,从我们村口伸向五十挑谷(一片稻田的名字),弯进桂花湾,绕过宋家坝水库,爬上观音崖,滑下葛家沟,钻进复兴老街,然后接上国道212线,直通学校门口。
那是数年前的事了,但我依然时常想起那些走路上学的日子,都说“人生如路”,我不就那样走过来了吗,这应该是我人生的一笔早年“财富”吧。
跑路上学当锻炼
学校要求同学们早上7点半到校开始第一节课――也就是早读;下午5点半放学――有时候会因老师拖堂或做清洁而放得更晚。而我们花在路上的时间来回就各需一个多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得早上6点起床,匆匆解决早饭后便立即上路。村里有几户家里大人外出打工去了,孩子们跟着爷爷奶奶过活,冬天里老人起不来,就得由孩子们自己煮早饭,所以比其他孩子更早――5点多就得起床了。也许,山村里的孩子都是在泥土里滚爬着长大的,对生存环境有超强的适应能力。下午放学回到家已经是7点钟左右,早已饥肠辘辘、腿疲脚软了,然后开始自己做饭,虽然都是些蔬菜、咸菜,但我们觉得那时的饭真的好香。
父母们说,反正都是些细娃,跑跑路全当是锻炼身体。现在想来,乡下的父母都是天生的“健康教育家”吧。
一路喊着乳名走
在上初中的三年里,每天早上,当听到公鸡的第一声报晓后,十几户屋里的灯就挨着挨着亮了。接着是一阵锅碗瓢盆的交响,然后便是大人叫孩子们起床的声音。那种叫喊不是一般描写亲情的文字中所述的“慈爱的妈妈,在枕边、在耳畔,用温柔的声音轻声呼唤”,而是立在灶屋的灶前,隔了耳房、堂屋好几堵墙扯着嗓子大喊:“二娃子,快起来!”“三丫妹子,吃饭喽!”这种叫喊声能穿透墙瓦,全村飘荡,把一些睡过头的孩子唤醒――因为他们家里没有这样的叫喊,如同我前面所说,他们的大人都外出打工了,就得自己煮早饭然后叫自己吃――比如村东的兵娃和东娃,听到这声音就急忙翻身起床。或许,听得久了,他们也把这声音当成自己妈妈的了。接下来便是各家开门的声音,掺和着妈妈的低声叮嘱。孩子们从村里向村头一边走一边挨个地召唤,那嗓音是跟爸妈学来的,底气十足又悠长飘远:“中娃,走喽――”“纱妹子,还没出来啊,走哦,要迟到哦――”。于是,孩子们陆续聚集,一路叫唤,惹得各家的母鸡、狗、猫、猪、牛什么的也跟着乱叫唤。
好一阵子的闹腾后才到了村头,大家彼此照着,确定十几个人都到齐了,便一起朝学校赶去。
火把照亮上学路
冬至过后,夜渐长昼渐短,早上出门仍是漆黑一片,下午放学走到一半就夜幕盖路了。于是得准备手电筒,赶早摸夜。但没过多久大家就发觉,电筒虽不贵,但隔三差五就需换电池或灯泡。常常一不小心就没电了或灯泡坏了,周围一下就伸手不见五指。于是我们想到了火把,村里人最原始的传统照明工具。且做火把操作简单,材料易得。早上出门时到草垛里扯出一个稻草来,分一支点着,其余的夹在腋下,一路走一路烧,一路烧一路叫。而且沿途要经过不少村子,若是燃料不够了也可随时得到充分的补给。
本来一支火把就可以保证三五个人看清路面,但我们非要一人一支,走到一起呼啦啦地烧,似乎那样才像上学的架势。而我仗着家里田多稻草多,每次都把两个稻草捆成一个抱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大把大把地烧。而其他的伙伴,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不甘示弱,一个个的都使劲地烧。十几支火把蜿蜒成一条小小的火龙,流窜于田间、跳跃于山梁,火光亮彻天际,什么野狗蛇虫的东西,老远便望火而逃。加之一路上我们边走边闹、边叫边笑,也就没了瞌睡、忘却了疲惫。不知不觉间便到了学校门口。
这是一条成长路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那个小小的村庄里所有孩子,早在他们仅十一二岁的年月里,便经历了上学之路的几乎所有忙碌、辛劳、疲惫,以及兴奋、欢欣和快乐。以至于在后来的――尤其是大学里的――优越舒适的寄宿学习生活中,每每遇到冷飕飕的早晨、雨绵绵的秋冬,以及其他一切可以作为我们赖床、迟到、旷课的借口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初中,想到那忙碌又喧嚣的早晨、寒霜里跳跃的火把、十二里长的崎岖的村道,便感到羞愧不已,即刻翻身起床,匆匆赶往图书馆或课堂。用初中时的上学激情,感染我的所有的上学之路――也感染我今世今生的生存、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