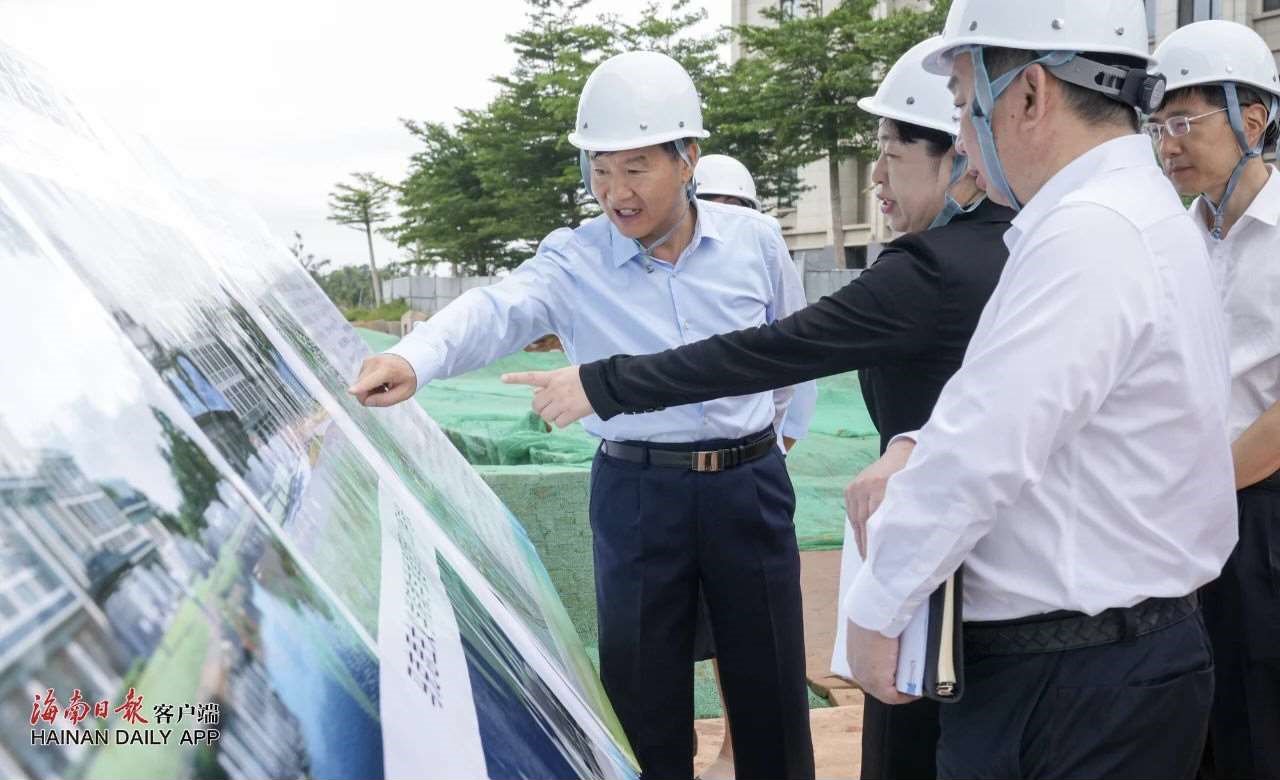“来迟了,来迟了!”老张笑着冲包厢里的人招了招手,回身把被雨淋湿的外套挂在衣架上,又悄悄用挂在那儿的另一件大衣盖住了外套上一块明显的水渍。
“迟到得自罚三杯!”
“该罚!该罚!”
老张忙离开衣架找近处坐下,装作无事发生。
这是大学毕业二十年的同学会,地点就定在学校旁边。
两杯酒下肚,老张的脸颊倏地烧起来。他望向窗外,这里曾是城郊空地,现在建成了一条熙熙攘攘的步行街。周末的夜晚,大街上尽是鲜活的年轻人,连带着这一块的夜幕似乎都比其他地方亮堂一些。
对面坐着的人不依不饶地让他喝完第三杯。老张忍住胃里的不适感,扬起笑脸冲对面的好哥们儿遥遥举杯,又一饮而尽。老张天生对酒精不耐受,而这个人大概已经忘了。
喊老张喝酒的人是他的上铺刘希,也是老张学生时代的好哥们儿。两人一起上课、吃饭、打开水,刘希给老张挡酒,老张就给刘希当恋爱参谋。不想毕业一别,竟没有再见过。
说没有隔阂是假的。
老张在心里叹口气。今天可由不得他心生疏远,他来这一趟,有正事要办。
是临出门前妻子千叮咛万嘱咐“不准由着性子胡来”“一定要拿下”的正事。
妻子肚里怀着第二胎,老张不敢惹妻子生气。其实,往深里说,他一直对妻子很是歉疚。妻子读书时是个美人,加上成绩优异,追求者众多,却偏偏看中了家世样貌平平的老张。
“我喜欢你踏实肯干的劲儿。”她说。
这个女孩婚后并没有过上宽裕的好日子,老张常常这样想。抬头看到妻子挪动着孕期庞大的身子操持家务,心里便一阵难受。
酒过三巡,老张心跳如鼓,不敢再喝,便使出惯用伎俩,出门找服务员要了一听雪碧。转头刚好看见刘希身边坐着的同学打着酒嗝往卫生间方向去了,立刻回身端起酒杯,闪身坐到刘希旁边,扯了扯刘希的袖子,把他的眼睛从班花那个方向扯了回来。
“兄弟,我有件事想求你帮个忙。”老张压低声音。
“什么事?有话快说。”刘希不满他打断自己在女同学面前的表演,神情中有几分不耐烦。
老张看得真切,一时不忿,想起妻子的话,又生生压下去:“听说哥们儿调进区实验了,恭喜啊。”
“哈哈,碰运气的,谢谢哥们儿啊。”刘希敷衍道,又转头看向班花的方向。老张不由得一起看过去,班花保养得真好,白腻腻的脸上一根细纹也没有。
老张还是犹犹豫豫地开了口:“那个,兄弟,我女儿今年刚中考完,成绩不是特别好……”
“成绩不好,读普高啊。”刘希埋头吃菜,并不看他。
老张越发窘迫。
“兄弟,刘哥!”他左右看看,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动作幅度压到最小,“孩子自制力差,想读个好点的学校,有好老师给管着,高考考个好点的本科。您给帮帮忙……”
刘希终于停下筷子,看了信封一眼,又看了看老张。老张饮酒后脸本就红得厉害,此刻仿佛是在蒸腾了的热气中憋着。他稍微别开眼睛,擦了擦额头上不存在的汗。
刘希再次夹了一筷子菜。
“哥们儿,不是我不愿帮你,现在制度严格,你分数不够就是不够。”他看着老张如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的神色,语气又缓和下来,“我给你想想办法啊,想想办法。”
老张如蒙大赦,直起身子来想道谢,又想起了什么,忙把信封往刘希怀里塞。
“都是好兄弟,你这是做什么?”刘希轻声斥责,又把信封推回来。几回合后,刘希勉为其难地收下了信封,声音带了懊恼:“跟我这么见外。”他端起酒杯:“来,咱哥俩再喝一个。”老张忙不迭地举杯,心里好像有块石头落了地,却又疙疙瘩瘩的,不得劲。
包厢里的冷气开得足,老张打了个寒战,一下子清醒过来。
眼前是双层铁架床,木头大桌子,头顶的小风扇吱呀吱呀,穿背心的室友窝在桌前吸溜泡面。角落里是一摞摞打包好的行李,地上散落着几本旧书。
门被踹开,刘希顶着刚洗完还在滴水的头发走进来,随手拽开他的被子:“别睡了,一个午觉从1点睡到4点,我也是服了。”又朝吸溜泡面的室友笑骂道:“马上要吃散伙饭了,你个没出息的还吃泡面?”
“我饿了,你管我?”室友顶了一句,隔一会儿又说,“这算是咱班第一次同学聚会吧?真没想到第一次就是最后一次。”
老张甩甩头,这个梦充斥着连最老套的电视剧本都不爱写的桥段,睡了一下午比醒着还累。
他从床上坐起来:“你懂什么,毕业之后吃的那才叫同学聚会,这顶多算同学聚餐。”又朝正在用毛巾粗鲁地擦拭头发的刘希踢了一脚:“今晚我破个酒戒,咱俩喝点。”
老张跳下床,对着墙上的镜子捋了捋头发。镜子里的少年意气风发,和所有22岁的年轻人并无二致。
挨了一脚的刘希冲上来,两人闹作一团。头发上未干的水甩在老张的T恤上,一块明显的水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