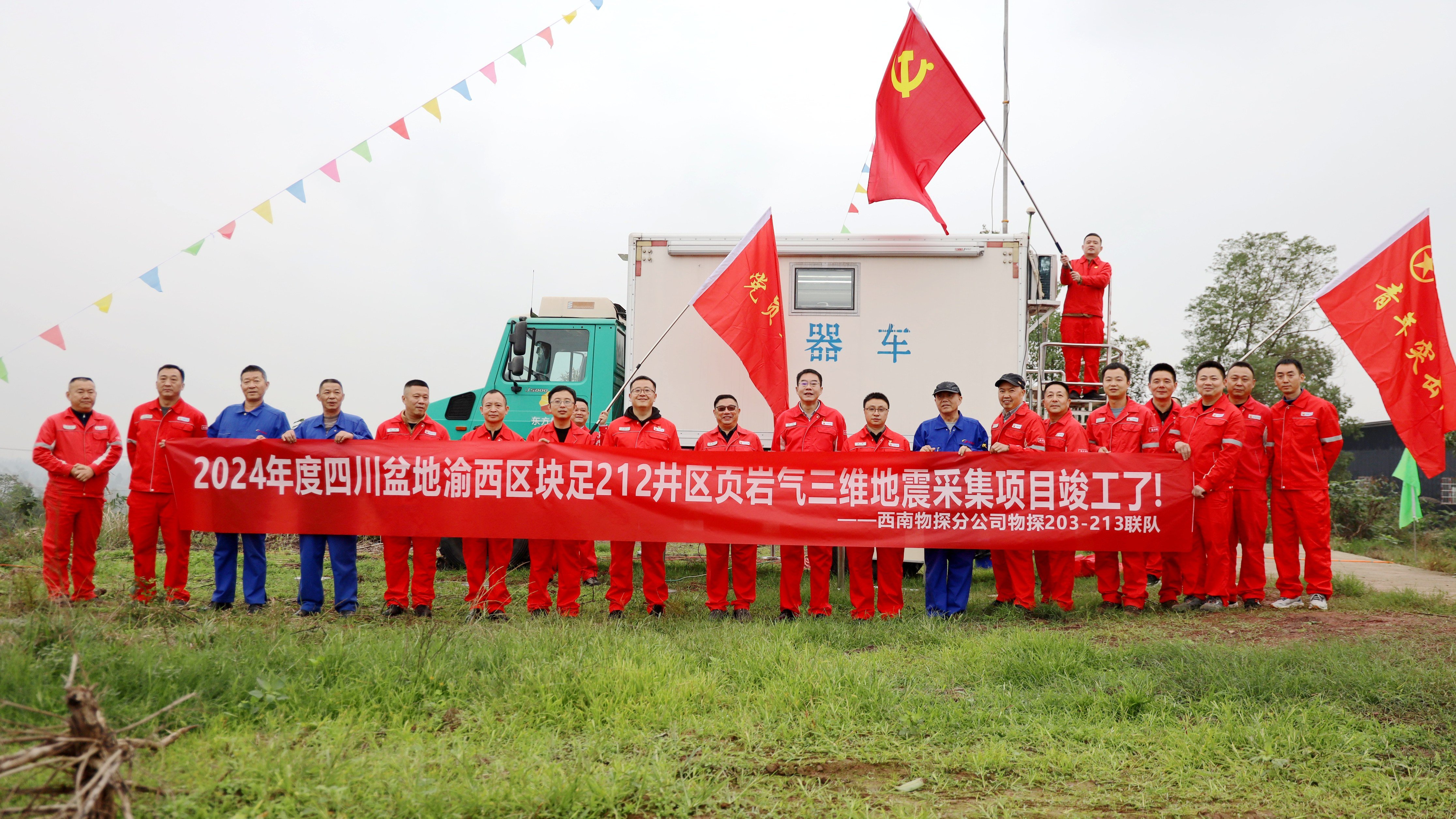编者按:且说时间是没有起点和终点的吧。如果说面人会说话,那阿莱想,在漫长的纠缠里,回望过去是陆瑶狭长影子下,一个老人所有的相思,走入未来的应是她自己罢。若不是这些时空碎片,若不是那顶红轿,那大概,齐明也没如今这般重新开始的勇气,而阿莱,也无法拨云见日明白面人的意义。
四
来过的那姑娘是村里的陆瑶。哦,就是家里做书画生意的。那年头她父亲出去经商发现书画艺术品赚钱,她们家也就是在那时发家的。在村里,她的家境还算不赖。
打听到这个,齐明也忐忑了好些时候。一来他与那陆瑶不甚熟悉,二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不知道她许了人家没有,总不能因为那鸡蛋,那人群中的一眼,就凑合过日子吧?嘶———面人刻刀划破了指尖。这已经是今天不知道割的第几道口子了。他心里空落落的,总感觉那股香气远了似的。
母亲进了门看见他正在发呆,指尖冒着血珠,案台上的刀晃晃悠悠,随时可能掉下去割伤脚。她问他想甚,是不是在想给鸡蛋的人儿。他支支吾吾半天,吞吐说出就是来过家里的那姑娘陆瑶。她也没多反对,自己的儿总是疼的。“阿明,刀。收拾一下,出来吃饭了。”齐明回了魂……
隔天齐母托人打听了一下陆家的情况,想着陆家姑娘要还没许人家,就提个亲。很快人就回来了,齐明也催着,还没等人歇下来赶上前就问。
“我喘口气儿。”媒人缓了缓,“难成咯,难成咯。”
这话一落,他就拖拉拉地回里屋,末了,他顿了一下,回头,“怎么难成?”终究还是不太甘心。
接着无非就是媒人诉说其他之类的,陆家说是吃怕了穷人的亏,想给女儿寻一个门当户对的。摇头便是对齐家的面人活儿看不上,是要过苦日子之类的云云。
后来,后来便没了信。他没再见过陆瑶,那股香气好像更远了。
可老天并不打算让这事儿结束。
齐明心里念着,他开始闭门。那段日子里,他对着那块手帕,思忱着那股香气,那离去的背影,以及她那双眼睛。他怕,他怕忘记这个感觉……
咚咚咚,有人敲门了。齐母不在,齐明好一会儿才出了去。开门便是那日思夜想的人。
“我,我明天,就嫁人了。”
他心晃了一下,勉强笑对,“你总归要出嫁的。”
“你真心愿意?”
他不想说下去了,手上还攥着他的工具刀,又刺了自己一下。
“你说话呀!”陆瑶哭腔渐浓,他心头又一紧,却也无奈,他不能做什么,他有娘,有家,还有那面人营生,何况他没有那个能力和勇气去博取他们的未来。他的眼眶里血丝饱满,转过头去,“你还是快回去吧。现在毕竟说什么都不合适。我,我,我确实没本事能娶你,我的顾忌太多。”
话一落,就像有玻璃摔在了地上,都是渣,连同陆瑶的心散一地捡不起来。
那日后的隔天,他早早就听见锣鼓鞭炮声。也是那时,他心中的那个女孩和桌上那一副火红盛艳的花轿也随着声乐在日光下发出刺眼的光拉成一道狭长的影子。
男婚女嫁,孝子为先。他也婚娶他人,两三年头,家计富足,倒也和睦。只是妻子难产,早早便离开了齐明。后来齐母也离世,他就独身一人。
再后来他听说,陆瑶独寡,也不是没生个一儿半女,但都早夭,她身体也渐渐破败,精神气不似从前。他去集市上谈些生意,路上偶尔也碰见,远远地,远远地,那眼神里有很多复杂的情绪。不用言语,似乎一眼就能看到很多。
五
打那日看了阿莱的“作品”,这小老头便心事重重。
他不在里屋捏那穆桂英了,也不去后园打理蔬果,倒是抽起了旱烟枪,偶尔对着孙女愣愣地发呆。有时候,阿莱叫唤了几声,他在里屋也好久不出来。她探了个头去看,就看见他趴在木台上看那箱子里的宝贝轿子。阿莱不知道,那副轿子原是有它的新娘的。
小老头突然变了样,阿莱有些担心。她去寻来阿峰大伯,想问个究竟。许是她年纪小?爷爷觉得对一小孩讲不明白什么,老一辈的情谊他自然会脱口而出。嗯,对,她想着。
“小孩,想吃大伯家的酥糖了?”
阿莱笑了笑,“不吃糖就不能来大伯家了嘛———”阿莱拖了长音,略带撒娇的余韵,“爷爷近来心情不太好,我想求求大伯找他下下棋啊,喝喝茶呀,干什么都行。他都不捏面人了,也不怎么说话。最近还把他那丑玩意儿,哦就是,他那枪杆子拿出来了。”
嘟哝半天,看着女娃灵动的面容,可可爱爱,齐峰许是晓得了什么。领着孩子吃完午饭回了去。齐明换了个地方发呆,躺在堂屋的藤椅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哼曲儿,嘴里时不时吐了烟气出来。
“阿明,丫头在我那儿讨了糖吃,你说你怎么让孩子馋着呢?”
“唉———”半晌,爷爷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摇了摇头。
“丫头,你先回房间玩吧。我跟你爷爷好好唠嗑唠嗑。”阿莱乖巧地回了西房,但其实她就是作势躲在堂屋隔边的过道。她打算偷听大人讲话。
齐峰拍了拍齐明的肩,接过他手里的烟杆,“想她了?也是,你这就跟她走后的那几天太像了。”
齐明吐出嘴里那一口烟末味儿,“阿莱真像她。又不像她。”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那时后来的事情———
齐明已经靠他的面人伙计什积攒了一些家用,他又独自一人生活,也没啥花销,日子过得还算滋润。那陆瑶可就不同,她一个寡妇人家,没了夫家,也没了子女,身体状况算不上好,过得清贫,叫人看了不免心疼。那时人们的闲话还是比较多的。齐明惦念着年少时的那股子喜欢,他想着照顾她,但困难重重。
陆瑶虽是独寡,可她心里也是还有着那个她送过鸡蛋的男人的。她能时常回想起他那时说不能答应她无力请求的表情,令人失望,却又叫她不得甘心。那个男人除了顾家,怕是眼里心里都是那面人。她喜爱他的那项手艺活儿,她也讨厌他那项手艺活儿。她知道他现在想对她好,但是她不想给他引来别人的闲言碎语,说他跟寡妇在一起了。
尽管如此,两人还是在一起了,再婚的礼节不是很盛大,但他承诺给她最好的体面。一个算是强求,另一个却满是担忧。并不是不喜欢了,生活的棱角磨得他们的感情出现了许多尖刺,容易磕碰。他很久没跟女子一起生活,所以倒显得越发拘谨。他的确顾着她,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想逃避一些琐事细节,他就继续捣鼓他的面人。
她是喜爱着的,她喜欢看他专注地去捏他的小玩意儿,精雕细琢,整个人精神勃勃。她也是埋怨着的,齐明开始不懂如何跟她相处,就好像家里住了个客人,尤其是当她生下阿莱的父亲以后,两个人的关系似乎就更加模模糊糊,有那牵着骚动的感情,但是又无语相对。
再后来,她生完孩子之后身体一直是不见好的,越发消瘦下去。他那时才会每天为了越发嗜睡的她多多讲一些话,张口闭口都是他的面人,他喜欢的,怎么做的,他想的种种。他很少表达对她的感情,甚至有一瞬间让人觉得,他心里几乎是没有她的,像他年轻时不肯带她走的那般模样,觉得这个人好像对感情就是那么平平淡淡,无所牵挂,除了他的面人。她听着,其实她觉得很幸福,也很知足,可他不知道,他太迟钝了。她在某段日子,阳光还不错的日子,把他们的家收拾了收拾,她翻到了被一个精致的木箱盒子装着的那个东西,她和她的红花轿。她也没跟他提起过,她把轿子放了回去,但她把那个新娘收了起来。
临了临了,那段日子就像是回光返照似的,她突然开始大病,口齿模糊,意识也不清楚,但她记着那顶轿子还有那个凤冠霞帔的年轻时的她。齐明为她擦身的时候,他看到她床头包着东西的手帕。他看见了,是“她”,她看到了。之后便是她离开前一定要那个东西陪她,她说,这样感觉年轻时她遇见的是他,她最终嫁的也只是他而已……
思绪拉得很悠长,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齐峰知道,齐明就是想她了,他也没多说什么其他的话,就两个人静静地在堂屋里时不时哼着曲儿。而阿莱,什么也没听到,她站累了,在侧门的地上睡着了。
六
晚饭时候,齐明去寻孙女,刚迈出石阶,就看到一只小脚露在那里,顺眼过去,阿莱猴儿似的靠在门上睡着了。
这丫头,也不知道会着凉。他想抱她起来。他尝试了一下,阿莱却被晃醒了。
“爷爷———”声音软萌无力,睡意仍浓。
“爷爷都抱不动你咯。阿莱你这小孩,睡哪里不好,等会儿生病爷爷可是要生气的。”
“好嘛。”她揉了揉眼睛,“要吃晚饭了吗,爷爷?”
“就是叫你吃饭的,小丫头片子。”
……
他看着吃得津津有味的孙女,突然冒一句,“你记得小时候你偷偷地翻我的箱子,摸了我的喜轿,被我狠狠教训了一顿吗?”
“记得。”女孩嘴里还有一口饭,说话奶声奶气的,“那是您……”她吞了下去,“那是您唯一一次凶我打我!”
“知道为什么吗?”他也没等她问,就自己回答,“那是我为你奶奶做的。我还跟你说过,这是我最认真的一次,是我所有面人作品里不许卖也不让人看的唯一一个。这轿子门前,原本是有个新娘的,但她带走了。多少年了,爷爷该放下的还是没放下,也凶了你,哎……”老人的声音开始有点沙哑,有点哭腔,“我老是觉得小阿莱像极了你的奶奶。你的眼睛,你的习惯,还有你对面人的想法。你的父亲或许是有那么一点像她,但没有你像……”
阿莱知道,爷爷是重感情的。但她没想过,那顶轿子是有个新娘的,她也不会知道爷爷到底与奶奶发生了什么事,但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七
我是陆瑶。准确来说,我是那个叫陆瑶的新娘面人。
我随着陆瑶长眠于地下,我离开了那座喜轿。其实,我竟是有些开心的。我在那个角落伴着齐明胶着的目光孤独着,这其实令我费解,但我又好像理解。
他没有给我掀开轿帘,我的动作像是还在等着些什么人,凤冠霞帔,迎亲彩礼,好一幅盛世,可是我周围的事物却很黯淡,开心不起来的那种。
我是他的新娘,但她不是。
我当然是听着她的冲天鞭炮声跟齐明在屋里“狂欢”。可惜我是个面人,我抱不了那个男人。之后的许多年,我看着他像个几乎没有感情的人,专注所有的面人制作,但是却再也没有做我时那股激情与钟情了。或许只有我知道,在他心里,对这份手艺的感情这么多年来是只增不减的。
那时兴盛的家伙什年代,靠手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做这个也不挣钱,尽管他独身,但终究生活还算不上太好。后来他娶了她,但他的感情在我感受而来在面人上好像多于她了。
或许是他不善言辞,但我好像也看不懂他了。
陆瑶看到了我,她把我收了起来,临了临了,让我随她而去。她对他说,她是喜欢穆桂英的,因为她的韧性与勇敢,这些勇气是我和她甚至他身上没有的。她那时意犹未尽的眼神,我至今历历在目。
所幸,我也终归于她,长眠地下,找到了我存在的意义……
八
晚饭后,爷爷拿出了那副喜轿,给了阿莱,“小阿莱,你不是想卖了它吗?爷爷现在把它送给你了。”
阿莱也没问,就接过那顶火红得有些刺眼的轿子。似乎,没有那么讨厌面人活了?
后来她自己把轿子收起来了。她想着,面人的故事不应该在她这里结束。
打那以后,她去西屋的次数也勤了。爷爷还是在捏穆桂英,有时,他会犯困得直接倒在工作台上睡着了。花白花白的两鬓,褶子纹路的脸让人怎么看都觉得年轻时应是个温润的男子。
她在他睡着时开始学习如何从雕刀的运用及细刻笔的拿捏还有手巧劲儿的训练来提升自己。她想跟他一起做完他最后的杰作———穆桂英。
爷爷钻研了那么多年的面人。
他捏了那么多的面人,记住了那么多故事。
最终,他也把他刻入了面人里。
她想着,她也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