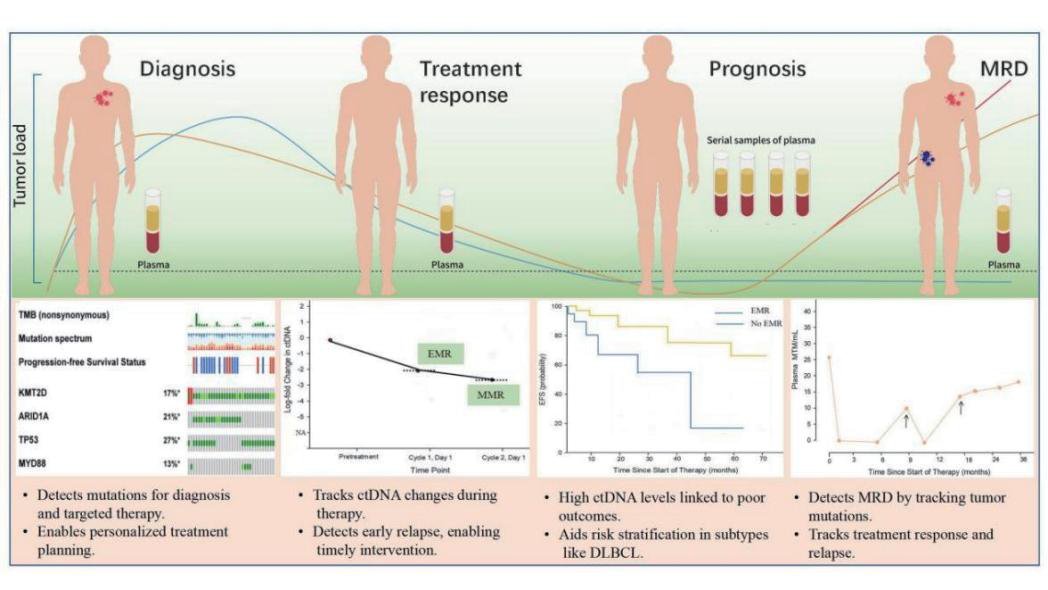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陶大镛先生1918年3月出生于上海一个工人家庭。他的父亲从16岁起就当了工人,长期在商务印书馆排字车间做工,家境贫寒。陶大镛先生从小就勤奋好学,成绩优秀,读完子弟小学后,接着上初中。但是,当他踏进初中二年级时,因父亲失业而不能继续读书。后来通过亲友的帮助,改为半工半读,勉强维持到初中毕业。这时,他的父亲要求他去工厂做工,但他并不甘心就此辍学,而是想方设法投考免费的学校,于是他进了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商科。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异,读到高中三年级上学期就提前毕业,进了一家电机制造厂当簿记员。他在工作中省吃俭用,同时自学数理化准备考大学。终于在1936年考取了学费较低的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
1937年,陶大镛先生的父亲和祖母在贫病中相继去世,日本侵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强占了江湾和闸北,他被迫逃难,步行到镇江,后到南京。这时中央大学已迁往重庆,他又经历了许多周折才到达重庆找到了学校。国难与家难的双重压力激发着他“为国民找寻出路”的情怀。1937年4月9日,当时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陶大镛先生就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中央储备银行的职责》,从此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人生历程。
也正是在大学读书时期,陶大镛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启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朋友那里借到一本列昂节夫著的 《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从这本书中得到了启蒙。后来,为了进一步从原著中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又托人从香港买来了《资本论》英文三卷本。利用暑假的时间,系统学习了这部巨著,并以卡奇(即从卡尔·马克思和伊里奇·列宁的中文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的笔名,在重庆《读书月报》上发表《我怎样读<资本论>的》一文,介绍他读马克思《资本论》的体会。显然,当时学习《资本论》,为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陶大镛先生考上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但时间不长,就赴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不久,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占领了香港,陶大镛先生历尽艰辛,返回内地,先后在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交通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除了用本名之外,还用大古、石人、奚石人等笔名,在 《广西日报》、《中国工业》、《时代中国》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官僚资本的罪恶,做了尖锐的揭露。
1946年至1949年,陶大镛先生在英国和香港期间,主要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他曾在《经济导报》、《文汇报》等刊物发表大量学术论文。这几年出版和成稿的著作有:《战后东欧的经济改造》、《新民主国家论》、《论马歇尔计划》、《社会主义思想史》、《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讲话》。总之,这一时期他的论著很多,内容涉及发达国家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年仅三十出头的陶大镛先生,在短短几年里就发表如此大量的文章和专著,不难想见,他的研究工作是多么的勤奋。1949年初,历尽艰辛的陶大镛先生与学界前辈、《资本论》中文版的译者王亚南先生相聚香港,两家同住一房的上下楼,朝夕相处,亲如一家。当时,陶大镛先生和王亚南先生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只能靠写稿度日。陶先生习惯于开夜车,而王先生则一向在黎明前奋笔。因此,每当陶先生刚刚躺下,楼上王先生家的灯便亮了,而在黑夜来临,王先生家的灯刚刚熄灭时,陶先生又在书桌前挥笔疾书了。真理的种子便在这两家灯火的交相辉映中得到了播撒。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一心向往祖国的陶大镛先生决定回国参加工作。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邀请,赴东北解放区,绕道营口抵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担任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计划处处长,主编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杂志《新建设》,同时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周刊主编。这一时期,他在全国十几个刊物上发表过大量的文章,著有《人民经济论纲》、《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等著作。
然而,人生的道路不是平坦的。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时年39岁的陶大镛先生,成为轰动文教界的民盟中央“六教授”之一,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解除了各种职务,被安排在资料室接受“监督改造”,使他蒙受极大的冤屈。但他并没有放弃信念和研究工作,仍然保持学者特有的专心钻研学问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学习,不厌其详地收集资料,默默无闻地从事研究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庸俗经济学在方法论 上的破产》及 《十九世纪末二十 世纪初庸俗经济学在价值论上 的破产》两篇学术论文。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陶大镛先生的错案也 得到改正。那时他虽已年过花甲, 依然精神矍烁,干劲不减当年, 他的著作也陆续得到发表。主要 有《社会主义思想简史》(1981)、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 特 征 》 (1981)、《亨利·乔治经济思想述 评》(1982)、《社会发展史》(主编1982)、《马克思经济理论探索》(主编1983)、《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主编1985)、《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1985)、《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主编1990)等。1992年,为了庆祝他执教5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陶大镛文集》上下两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成就。
经济学家的学术观点和他的政治信念是分不开的。陶大镛先生立志终身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正与他信仰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发表的十几部著作和百余篇论文,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写的,还是新中国建立后写的,是在顺利的岁月里写的,还是在挨批受压的逆境中写的,都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坚定的。而坚贞不渝的信念正是他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力量源泉。
有一个鲜活的例子可以看出陶大镛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感情。经济学家关梦觉是陶大镛先生的至交好友,1941年,他借走了《资本论》卷一,约定短期归还。孰料未几“皖南事变”爆发,两位老友顿失联系,一晃近十年之久。1949年,两人终于得见,欣喜之余,陶大镛先生言语间满是对心爱书本的牵念。而此时,这本《资本论》尚被关梦觉交托他人保管。两年之后,关梦觉特意携书北上,完璧归“陶”。一丢十余载,转手几万里,这部巨著终于“回家”了。陶大镛先生专门撰文,以作纪念:“那时的喜悦和激动,实在无法用笔墨来形容”。至今,这卷充满传奇色彩的《资本论》还珍藏在陶先生的书斋里。
陶大镛先生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是把《资本论》中的一字一句,都奉为万世不变的信条。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我们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科学体系,必须正确地运用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由他主持的国家“八五”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进行研究的。由于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就,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时,一致选举他为副会长,后任名誉顾问;他还被选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术顾问。
世界经济研究方面,陶大镛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出版了《世界经济讲话》(三联书店1950年)和《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中华书局1950年),这两本书是目前能检索到的我国学者有关世界经济的最早的专著,该书系统地阐述了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方法、基本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为这一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他又在 《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发表一篇长文 《论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对世界经济研究的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首任会长钱俊瑞曾称陶大镛先生 “是我国最早提出并从事世界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所以,在1980年成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时,陶大镛先生被推举为副会长,1981年建立学位制度以后,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陶大镛先生成为我国首批世界经济博士生导师。为了更全面反映陶大镛先生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学术成果,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陶大镛文集》(世界经济卷)。
由于陶大镛先生在学术界的重要影响,他曾出席1956年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参与制定《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出席1979年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制定《1980—1985年经济科学发展规划》;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曾任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90年,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陶大镛先生 “国际荣誉勋章”和证书;1991年当选为剑桥传记中心顾问委员会名誉委员,入选《世界首批五百名人传》;1993年剑桥传记中心授予他“二十世纪成就奖”,还入选多种国际名人录。
桃李滋荣 杏坛春暖陶大镛先生一生热爱教育,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建言献策,并身体力行,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杏坛舞翩迁”。
陶大镛先生的教育生涯还要追溯到1942年。当时日本侵略占领了香港,陶大镛先生虎口余生,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广东坪石镇。在坪石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的王亚南教授。由于两人对《资本论》有相同的追求,在王亚南的推荐和热心帮助下,陶大镛先生被聘为中山大学讲师,开始了他的教育事业。
随后,陶大镛先生于 1943年至1944年在桂林广西大学经济系任副教授,1944年至1945年在重庆交通大学管理系任副教授,1945年至1946年在成都四川大学任教授。在这几年里,陶大镛先生讲授过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史、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原著选读、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和经济数学等课程。他从教三年,就由讲师、副教授提升到教授,那时他年仅27岁,这在我国教育界是不多见的。
1946年秋,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陶大镛先生以进修学者的身份,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经济研究,1949年初返回香港,在达德学院商经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辅仁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师范大学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师资的培养,成立了政治教育系,1954年陶大镛先生被聘为教授,并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为政教系第一届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由于教学科研成绩突出,1956年他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1979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北师大决定把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政治教育系分为哲学系、经济系和马列主义研究所。这时,陶大镛先生接受了筹建经济系的任务,并任系主任。他虽然年过花甲,依然忘我工作,积极组建师资队伍,制定经济学人才培养方案,很快就建起了全国师范院校中第一个经济系,为全国其他师范院校做出了榜样。陶大镛先生作为北师大的经济学科带头人,十分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高,鼓励教师开展科研工作。在陶大镛先生的带领下,北师大经济学科逐渐成长,发展壮大,如今的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已成为我国经济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陶大镛先生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深知我国教育的现状、问题和症结,他在许多会议、论坛和刊物上发表的教育言论,综合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教育不是商品,不能推向市场。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本身也是“商品”,学校也是市场,深化教育改革,就必须“把教育推向市场,面向市场”等等。陶大镛先生认为,“不可把商品经济的规律盲目地引入教育领域里来”,不能把“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教育商品化”混为一谈,也不应把“教育必须面向社会”说成是“把教育推向市场”。
实现“科教兴国”必须“国兴科教”。他强调“科教兴国,教育为先”,科技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教育,发展教育。他针对我国教育拨款一直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情况,多次呼吁政府应该对教育加大投入,每年至少要从GDP中拿出4%投在教育上。
发展教育关键在政府。他认为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因此发展教育的责任主要在于政府。陶大镛先生在任全国人大常委期间,长期参与立法工作,《教育法》的颁布就包含着他诸多的心血和建议,比如关于教师待遇的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水平,并逐步提高。”对这一条,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此外,陶大镛先生还和其他学者共同倡导设立了“教师节”。
稳定师资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关于这个问题,陶大镛先生曾提出六条措施:第一,大幅提高各级合格教师的劳动报酬,务使教育系统的平均工资水平高于12个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第二,除职务工资和各项规定的生活津贴外,教师可另加教龄津贴;第三,凡满30年教龄的教师,退休后可享受全额工资待遇;第四,民办教师的工资不但要按月兑现,而且要能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第五,兴修教师宿舍楼,使教师能安居乐业;第六,师范院校的学生可免交学费。
虽然岁月过去了多年,陶大镛先生提出的这些措施仍然掷地有声,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国为民 大爱无形陶大镛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1939年,他在中央大学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团”,担任过团长,同时还发起并领导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苏问题研究会”,放映苏联电影,举办苏联生活图片展览,还经常举行座谈会、报告会,并曾邀请周恩来以及邹韬奋、潘梓年、钱俊瑞等到重庆沙坪镇中央大学做报告。由于他参与爱国进步活动,曾受到学校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记恨和监视。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四川大学任教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他曾与彭迪先和李相符教授一起,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营救被捕的学生,因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这就是当时在四川大学发生的“三教授事件”。1946年至1948年,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做访问教授,结识了一批留学进步人士,声援国内的人民解放战争。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筹建了中国民主同盟英伦支部,任民盟英伦支部负责人。在那个时候,追求社会主义是许多革命青年的崇高理想,但很难找到有关社会主义的中文参考书,陶大镛先生利用身处英国的有利条件,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潜心研究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流派。1948年,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100周年,他全力以赴地在短短两个月内撰写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一书,寄回香港士林书店出版 (全国解放后又由三联书店发行过三版)。
此外,他在留英期间,还对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状况做了深入的研究。主要根据东欧各国驻英使馆提供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写了许多通讯报道和研究文章,发表在上海和香港的报刊上。他身居异国,以学者的身份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宣传东欧新民主国家改革的情况,描绘新中国的未来,这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9年春,国内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一心向往祖国的陶大镛先生,响应党的召唤,决定回国工作。他在离别伦敦时,特地到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献了一束鲜花,以此表达对马克思的崇敬和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携带全家四人克服重重困难,冒着巨大风险坐船回到香港,在进步教授会集的达德学院等待时机准备北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夕,他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的邀请,辗转来到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陶大镛先生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依然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
从20世纪80年代起,陶大镛先生担任了多项重要社会职务,历任第八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四、五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第一、第四届北京市委副主委,第五、六、七届主委;民盟第一、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第八、九届中央名誉副主席。
在他主持民盟北京市委工作的十几年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努力发挥参政党职能作用,围绕北京市的“两个文明”建设,广泛组织座谈研讨,对北京市“八五”计划纲要、“九五”计划纲要、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政府工作报告、重要人事安排、廉政建设、亚运会的筹备工作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采纳。他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加强民盟北京市各级组织自身建设,团结和带领全市盟员为促进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陶大镛先生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兢兢业业履行人大工作职责,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对北京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及有关立法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在立法工作中,充分听取和反应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主持完成了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北京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工作。他注重监督实效,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开展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检查,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北京市的民主法制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陶大镛先生在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期间,担任《群言》杂志的主任编委十余载,他不辞辛劳,尽心竭力,把这份月刊办成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刊物。他多次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召开的座谈会,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发挥了积极作用。
就在陶大镛先生因病长年卧床期间,他也念念不忘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发展大业,时常让家人和学生给他读报、讲述外面发生的事情。就在住院不久后的一天,先生谈及中国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竟至老泪纵横:“研究了一辈子经济,还没能让所有农民都过上富足日子,我心里惭愧啊!”听到先生借人工喉哽咽发声,连护工都没能忍住眼泪。
……回顾陶大镛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开拓奋进的一生,是令人敬仰的一生。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在长达7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始终不渝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为我国的经济科学研究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和才华;陶大镛先生终生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直抒己见,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陶大镛先生虽历经坎坷,但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心系祖国,竭力维护祖国统一,忠心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如今,陶大镛先生离我们远去了,但先生的高风亮节,厚德大道,将永垂后世,千年绵长,万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