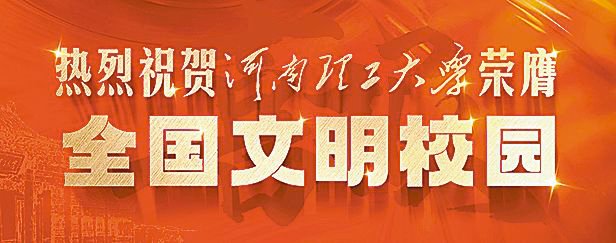孔雀洞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佛教藏经洞。位于石景山山腰净土寺碑亭以北。一间石室, 坐北朝南, 高有二米, 室内面积有五、 六平米。它是南开门, 北墙上有一尊石佛, 地上铺一长方形石板, 穹顶, 左右有转角台阶, 可以登上晾经台, 台北有一石洞, 人工凿刻而成, 洞中北墙有三个佛龛, 已无佛像,但石刻纹饰还在。文物爱好者金宝岩先生曾对石室多次进行过考察, 认为下面可能还有洞穴, 晋唐石经还在的可能性极大。学者关续文、 李新乐、 王荣华等对此进行过研究。市文保协会会员张文大先生也曾进行过专门的考察, 并在去年九月的 《北京文物报》 上发表 “云居金阁联袂藏经” 一文。他们的踏勘考证, 似乎更加实在, 更加可靠。
孔雀洞是石景山上古刹金阁寺的藏经之处, 这一点, 古籍中早有明文记载。明代《宛署杂记》 提到: 山上有元和四年碑, 日久难辨。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元和四年即公元809年。那碑文的内容应为金阁寺的藏经史, 可惜已看不到了。但明代的净土寺碑文还在, 上面载: 金阁寺自 “晋唐以来,所藏石经碎而言断, 岩穴鲜有存焉。 ” 这可证明金阁寺创建于晋唐, 那时候就在孔雀洞藏经了。而房山云居寺的藏经史, 只能追溯到隋炀帝时期, 也就是说孔雀洞的藏经史, 比房山云居寺早三百年左右!
明代的净土寺碑文不是向壁虚造, 而是引用了原有的另一古碑 “刘师堰石记” 。刘师堰, 即三国时期刘靖所修戾陵堰。刘师堰石记, 即指堰上的一块古碑。据北魏郦道元所著 《水经注》 一书, 那堰修在石景山下, 堰上有 “遏表” , 应即净土寺碑文所说的 “刘师堰石记” , 或略晚的关于戾陵堰的一通碑记。那碑至少立于辽金时期, 因为戾陵堰唐末已毁, 再晚的话撰碑人对戾陵堰的历史,很难说清楚。净土寺碑文的作者许用宾, 又称之为 “古” , 距明末应在数百年以上。许用宾对那碑的内容耳熟能详, 所以才记到了净土寺的明代碑上。
孔雀洞得名与佛教有关。佛教的发源地古印度历史上有孔雀王朝, 创建者阿育王曾为佛教传播护法, 所以他成了佛教的护法神之一。佛经有 《孔雀明王经》 , 描述孔雀明王为女性, 有四臂, 后背有雄孔雀的漂亮羽毛, 坐莲座上, 莲座又驮于孔雀背上, 十分威武美丽。此像, 在古印度佛教造像中还有遗存。此神能除病灭灾, 镇定天变地异。他来保护藏经, 是金阁寺的佛教徒们求之不得的, 因而孔雀洞才以孔雀为名。唐代以后石窟叫孔雀洞的寥寥无几, 可为石景山上孔雀洞历史悠久的又一佐证。
孔雀洞藏过何经? 《日下旧闻考》 载: “孔雀洞左右门上截题识曰,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 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敬造, 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建。下截刊佛经语。其地当石经台之阴, 殆藏经处也。 ” 可知, 藏的是唐代刘相公所刻的 《佛本行集经》 , 藏地在石经台下面, 即石室之内。该经有 60 卷, 需150块刻石才行。这是房山云居寺所没有的, 很可能还藏于石室之下的真正孔雀洞内, 我们将拭目以待。
孔雀洞在唐代进行过扩建或重修, 扩建人应该是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有学者推测, 刘相公即是唐宪宗时期刘济的次子刘总, 笔者也持相同观点。因为阿育王历史上是杀兄即位, 后皈依佛门, 刘总也有杀兄弑父的经历, 这应该是刘总把此洞府名为孔雀洞的重要原因; 此外, 现在孔雀洞内的佛龛明显是唐代风格, 洞府的规模不小, 如果不是有一定权势和财力的人所为, 不会修得如此壮观。
唐代的元和十四年 (819) , 当时的幽州卢龙两节度使正是刘总。据 《资治通鉴》 记载: 元和五年 (815年) , 刘总的父亲刘济攻打王承宗, 派大儿子刘绲留守幽州, 次子刘总带兵驻扎饶阳。赶上刘济生病, 刘总就联合张杞、 成国宝毒死了父亲。接着, 又假传父命把哥哥刘绲乱棍打死, 自己掌握了割据不见地区的军政大权。弑父杀兄的刘总做贼心虚, “心常自疑, 数见父兄为祟。常于府舍饭僧数百, 使昼夜为佛事” 。处理完公务,他就挤进和尚堆里跟着做佛事, 有时自己就躲进一个房间, 经常被剧烈的心跳惊醒。到了长庆元年 (821) , 他实在受不了精神折磨,就向中央坚决申请出家当和尚, 并把他的住宅当做佛教寺庙。皇帝给刘总起了法号大觉, 命名他的住所为报恩寺……命令还没到, 他就剃了光头正式皈依佛教, 还杀了挽留他的十多个将士, 交出印信逃的不知去向。3月27日, 刘总在河北定县境内去世。
这样一个人来修石景山上孔雀洞, 符合逻辑。石景山上的孔雀洞, 现存在较完整,也是石景山上所存洞府中最大的一个。石室内石佛, 衣袂飘拂, 面容丰满, 有唐代风格。石室前脸上方的左右两侧有石龟, 虽已无头, 但雕刻极精, 掩映在古柏根部, 不易发现。洞口还有不少雕饰的石构件, 可以想见其当年的宏伟气势和在北京佛教史上的辉煌地位, 有兴趣者不妨前往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