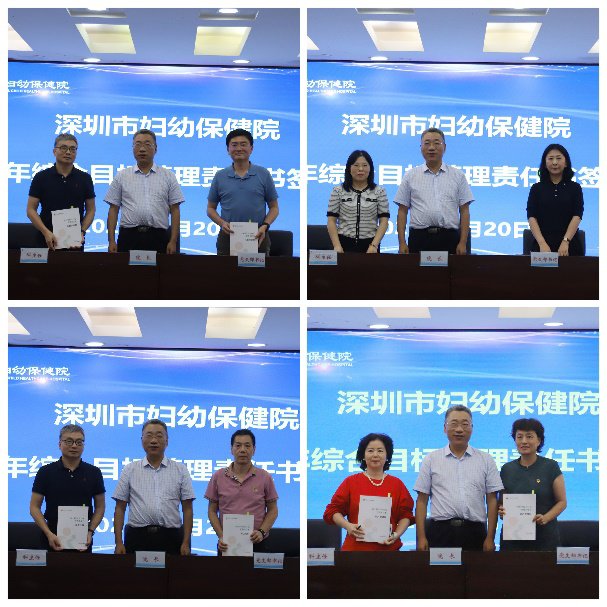天气越来越热。我总是想起那个姑娘,那么清冷的一个人,仿佛能消散这个季节所有的燥气。真不晓得聒噪的五月,怎么生得出那么安静、那么灵气的姑娘?清朗朗的,像初春的翠竹,娇嫩且俊秀。
我十三岁认识她,那时她还是个白嫩的小姑娘,一手字写得行云流水。我向她借画册,她细长的眼斜斜地扫过来,一脸“生人勿近”。此后数年,这都是她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但有时,你不得不相信缘分。她生得清冷内敛,而我年少时,就差没把“张扬”二字写在脸上。就是这样不搭的两个女孩儿,一路走来,成为旁人羡慕的好友。
她符合我对古代所有才女的想象。她填《如梦令》的词:夜语宴宴休,闲听簌簌雪漏,怎够怎够,风雪未及纸厚。我看了许久,将它抄在日记本里。张可久的小令里写“半纸功名,风雪千山”,可她偏偏说“风雪未及纸厚”。怎够怎够,这千山的风雪,十年的苦读怎抵得了功名?分寸也抵不得。这时我才晓得,这个姑娘是有执念的。她想呆在象牙塔,从春到秋,从青葱年少到晚暮欲垂。
我记得中考前出成绩,她绷着脸,站在楼道里突然哭出声来。我也记得高考前的无数个深夜,她挤在人堆里仰着头听老师讲题。这个年纪,太多同学把好胜写在脸上,可她不是。她永远挂着温润润的笑容,慢悠悠地在教室和宿舍间穿梭,用脚步不断丈量两点一线的距离,是一个沉默女孩儿最坚定的态度。我记得她想去的地方,记得她囤的那些书,记得她密密麻麻的笔记,记得她笑得狡黠,自信地表示:“我想去当历史老师,误人子弟。”
又是一年高考日。亲爱的姑娘,愿你十年风雪换一纸功名,他日站上三尺讲台,小议稗官野史,高谈圣贤群雄;在春秋战国间纵横捭阖,在三国史册里舌战群儒。前路虽远,明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