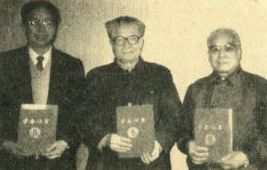十斗粟的姥姥
○赵雪纯
“把这团白线带着吧,这是你出生时姥姥特意给你缠的,说是12岁之前用完给你消灾。但你小时候我老是忘,要不有可能你初中后就不用受那么多罪了。”
“好吧,姥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这是上大学前收拾东西的时候,妈妈从生锈的铁盒里拿出来一团白线时对我说的话。姥姥是上个世纪的人,属于白砖青瓦平房的黑白片时代。她是历史的亲历者,但确确实实又是历史洪流中的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张妈,这是这个月的工钱,你拿着吧,也算是路上的盘缠。”
“夫人,那你怎么办啊?老爷被抓走了,小姐才5岁,小少爷也还在喂奶。”
夫人望着逐渐空荡的大宅子,默默念着“活着,就总会有办法的。”张妈含着泪,做完了最后一顿饭给小姐送去,看着她开心地吃着,那是她最喜欢的生煎包。“小姐,以后要多帮着夫人啊。”小姐咬着油浸浸的生煎包,笑得很甜,就连那声在几十年后还在张妈脑海中回荡的“嗯!”也很甜。那年的天空很高、很蓝;白云很轻,像街上打的花糕;溪水清冽,可以看到溪底的五颜六色的鹅卵石。
小姐,就是我的姥姥,而夫人是姥姥的母亲,背景是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地是血色的,人是复杂的,姥爷是被日本人抓走的。那时的平民百姓不关心今天是哪个皇帝,明天是哪个总统,不关心是封建还是什么革命。他们,只求能填饱肚子,仅此而已。姥姥的父亲是富甲一方的地主家大少爷,夫人自然也是名门的大家闺秀,从小被伺候到大,经媒人介绍,门当户对嫁到地主家。但世事纷乱的年代对谁都是公平的,皇帝在逃,官员在逃,老百姓也在逃,家产也不过是活得长短的一个衡量物罢了。
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下成长的夫人,在老爷被抓后便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她不会经商、不会操持家务、不懂茶米油盐,但知道家产可以卖钱。于是,庞大的宅子一点点地被变卖,家里的仆人一个个地减少。先是那些放着看的宝贝没了,够一大家吃两天的饭;接着是后院的偏厅没了,家里人又可以吃上饭了;再接着,小工都给差遣走了,丫鬟也都打发走了,但走时都给够了盘缠。闭眼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早太阳的年代,谁都不容易。最后的最后,跟着夫人来的张妈也不得不送走,夫人又怎么舍得。张妈一手把夫人养大,又操持着这个大宅子里的前前后后。张妈交代完家里的事,便头也不会地消失在巷子里。可这个只剩下夫人和两个孩子的家还能有些什么事呢?无非是小少爷几时需要喂奶,小姐最喜欢吃的生煎包怎么做,家里还有多少粮、多少银子……夫人瘫坐在正厅椅子上,望着堂屋前的庭院,呆呆地望着,望着。直到少爷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把她从恍惚中拉回来,从富贵梦中拉回来,活生生地扯到现实的挣扎中。堂屋外,天已经黑了,星星亮的寒心。“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夫人想着,哭着,但回应的只有两个孩子的哭声。砸了碗,撒了面弄出来的晚饭,小姐却嫌弃地扭过了头。夫人伸手就是一巴掌,小姐哇地哭了,夫人却也跟着哭了,“囡囡啊,娘不好,娘对不起你,娘也对不起你弟弟。”夫人跪着,抱着小姐肆意地哭着,哭着近两年的心酸,哭着世道的艰难,哭着自己的无助。小姐看着这一切,噙着泪,一口一口把饭咽下去,有了自己第一次自行回房。堂屋只有夫人还跪着,在跳动的烛火下,影子一闪一闪,在地上拖得老长。
镇上的人都在议论,昨天走过一群人,穿着白卦,带着红袖头,提着红灯笼的人;今天是一群拿着硬杆子,穿的一模一样的人。人们跟看戏一样,看着一群群的人来了,一群群的人又走了。街上的乞丐则会趁机把碗伸上去讨口饭吃,但得到的往往是粗鲁的斥骂或是结结实实的一脚。日子就这样过着,在饥一顿饱一顿的边缘。街上的乞丐是这样,逃亡的皇帝也这样。所谓的西方立宪宣扬的平等,竟在那个年代得到了哭笑不得的实现。那是个充满变数的年代,今天这个人当皇帝,明天却变成那个人。那是个是非不分的年代,一群人嚷嚷着民主,但都督过着皇帝的生活,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罢了。既然这样,今天拥有的可能一瞬间就会成为别人的,哪还有什么励精图治,人生苦短,今朝有酒今朝醉才是活着。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千年不变的亘古真理。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稍微有点家产的,一点点衰落。没什么家产的,想着反正就这样了,真可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不论怎样,都是一天盼着一天,一天熬着一天。对于历史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夫人自然也不例外。姥姥11岁那年,家里最后只有堂屋和卧室两间房。殷实富足的地主家,也走向了落灭的边缘,谁知道那些托人变卖的宝贝别人暗地里抽掉多少钱呢,就那样一顿顿过来了,就这样一顿顿过不下去了。夫人看着渐渐长大的小少爷,心里想着“总要给我的儿留间房吧,不然以后怎么娶妻啊。”但夫人又能怎么办呢,这几年厨艺倒是有点长进,可挣钱哪是女人干的呢,家里的东西卖完了,两间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卖了。夫人又坐在那个正厅的椅子上,看着堂屋外的白月光,只见那月光更冰冷了几分。
于是,街边的乞讨队伍中多了一大两小三个人,依稀可以从他们那褪色的袍子中看出曾经富贵的象征。这样的日子,就更加不知道下一顿在哪。也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来了一个人,乡绅的打扮。也不知他们怎么商量的,也不知是夫人自愿还是那个乡绅要求,那个年代的事,谁记得那么清呢。反正结果是,11岁的姥姥以十斗粟的价格卖到了李家当童养媳,夫人和小少爷再也不用上街乞讨了。那时的女儿家,哪有什么愿不愿意,那时的人们,哪有什么情感,都是大洪流中麻木的面庞。11岁的姥姥,早已看惯了这世间的人情冷暖,早已明白了自己总是要为弟弟而牺牲的,但或许是个好人家呢。也但愿是个好人家吧。
“小妮儿,我今天上街给你带了好吃的!”
“街上有什么好吃的啊?”
“街上好多好吃的啊,有生煎包。”
妈妈说,每次姥姥上街都会给他们带好多好吃的,有村里买不到的糖,有村里买不到的生煎包。妈妈是姥姥的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所以他们叫妈妈小妮儿。李家,是村里几世的书香世家,是日本人来扫荡时逃过一劫的幸运星,但后来也败在了文革,那都是后话了。姥姥也算是嫁到了好人家吧。但历史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的,姥姥作为童养媳,半个媳妇半个仆人在李家养着,等着她嫁给大少爷。可谁知国民党又来抓壮丁了,大少爷也被抓走了,姥姥就按排辈嫁给了二少爷,也就是我的姥爷。在妈妈的讲述中,姥姥知道很多村里的妇人不知道的事情。姥姥会告诉他们拿钱可以去街上买吃的,这个世界上除了一日三餐还有零嘴,会心疼跟着姥爷下地的孩子们,等姥爷出去好一会儿了才叫他们起来。妈妈说在这个家里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反而他们都疼爱最小的小妮儿。就连妈妈上街打醋撒了,姥姥也没有一句责骂,只是再给一样的钱,让妈妈再去打一次就好,用姥姥的话说是“东西没了还可以再买。”在妈妈的记忆中,姥姥是那样的亲切和蔼,是那样的勤劳贤惠,也是那样的知书达理,更是那样的波澜不惊。
但是伤痕却是存在的,就像历史就在那深深的烙着一样。妈妈讲到,一个夏日的中午,蝉鸣随着微风一阵阵的。妈妈躺在姥姥旁边睡午觉,突然被姥姥拍醒,只见姥姥一身冷汗,瞪大了眼睛,惊慌失措地喊着“快跑!快跑!日本人来了。”妈妈半梦半醒的脸上满是疑惑,只有飞机飞过的声音还在空气中回荡。姥姥定睛看一下这熟悉的院子,才明白,不会再有什么日本人来了。她呆呆地望着,亦如四十年前夫人望着白月光那样迷离。
姥姥2003年去世于食道癌,据说,姥姥生前叫的最后一个人,是我。但是那时我不在姥姥旁边,妈妈怕姥姥瘦的不像个人的样子会吓到我,妈妈怕我在还不懂什么是死亡的年纪留下心理阴影。但后来,我却清楚地记得,我去看姥姥时,姥姥颤颤巍巍地从堂屋里给我端了一碗米花。我就坐在堂屋门口竖着摆的枣红色桌子上,穿的是黄色圆领衫和黄色马甲。那是我6岁时的衣服,“可能姥姥想你了,给你托梦了吧。”妈妈这样说道。或许吧,我依旧是姥姥最疼的那个小外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