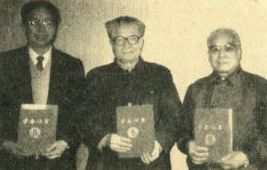“自然状态”的法哲学意蕴——对话卢梭与老子
纵览中西学术史,“自然”是美学与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人类对自然的体悟塑造了生命的理性逻辑与审美情趣,对自然的多向度阐发则建构了现代科学的伦理基石。在多元学科的语境下,“自然”有着截然不同的释义和功用。本文着眼于法学理论视角下的“自然状态”,对比分析近代西方与古代中国有关“自然状态”的法律思想,以卢梭社会不平等理论与老子小国寡民政治理论为焦点,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与《道德经》为文本依傍,对比中西法哲学自然观的异同,解构法哲学思想下的政治乌托邦,从而揭示“自然状态”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独特含义与文化内涵。
卢梭的“自然状态”理论
英国古典政治学家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处于所谓原始的无尽战争之中,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以满足温饱而疯狂掠夺厮杀。人类为了终止混乱无序的生存状态,而走向和解、缔结契约,将一些私人权利收归公共管辖,以此过渡到国家并产生政府。“自然状态”就是用来解释国家、政府与法律起源的一种理论假设。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使得“自然状态”理论进一步发展,洛克的“自然状态”理论指出人与人之间是自由平等、相互独立的,这种状态取决于人生而具有的理性。
在反思前辈法学家思想的基础上,卢梭认为一个人想要找到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真正起因,只能摒弃他后天习得的知识,从人类文明尚未诞生时的生存状态进行观察,前人所谓的“自然状态”,不过是对人类已经失去自然本真后形成的社会状态的描述。因此卢梭选择走进大自然去找寻所谓的“自然状态”,通过对自然界生物的观察,认识到在本身不具有文明和社会等级的动物之间,也存在着不平等,即自然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亦存在于人类之中,但人不同于动物,人类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平等——精神或政治上的不平等。第一种不平等是自然所决定的,而第二种不平等非经人们认可无法产生。区别产生的原因在于人拥有“自我完善的能力”。
正如《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书中所言,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类社会迎来第一次变革——建立家庭、拥有私有财产。卢梭认为,打破社会自然状态的稳定的罪魁祸首在于铁和小麦:人类偶然地开采了矿石,偶然地播种了小麦种子,从此诞生了冶金和农耕两种文明。由于农耕和冶金都需要人类劳动的投入,因此人们对种植和冶炼所得就会产生占有的欲望,且愈演愈烈。同时正常情况下,出于自己财产不被侵犯的愿望,人们也会自觉与他人的劳动所得保持距离。自从需要一些人去炼铁和打造铁器起,也就需要另外一些人去生产食物以养活这些人。人们逐渐认识到,可以用铁器换取食物,于是产生交换;产品交换的发展大大推动了铁制农具的生产。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可供交换的东西不断增加。在产品交换的过程中,受益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体力过人或头脑聪明者,他们使社会财富更多地流向自己。聚敛财富与欲望增强是一个死循环,一旦私有制度出现,则这一循环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去。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结尾说:“我们可以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
由此可见,在卢梭的政治观点中,自然状态位于私有制产生之前,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初级生存环境。
老子自然哲学观与卢梭的异同
有学者指出,卢梭钟情于自然状态中人类生活的样式,认为每个人都无私心、对邪恶毫无所知,无彼此之分的观念,所以也根本不需要去剥夺别人的财产来满足个人的欲望;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国是:国土小,人口少,由于没有欲望,故人类社会中并无“机巧”的存在,生活简朴合于自然秩序的社会状态。
从二人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来看,卢梭与老子所主张的理想社会均为小国寡民的类型。卢梭是法国人,其生活的社会是中世纪末期,社会矛盾突出,弊端非常多且严重,整个社会充斥着压榨、掠夺、腐化和堕落。老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周王朝式微,诸侯征战,统治者横征暴敛,社会混乱,世风日下。二人都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同样目睹了掌权者由于欲望膨胀而实施剥削、压榨的行径,相似的社会生活环境,使二人都培养出了对人类原始社会状态的怀恋和希冀,在政治理想上倾向于自然而然、小国寡民的社会。
从二人对政治的道德伦理批评上看,卢梭与老子都称赏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指出“如果大自然的本意是要我们成为健康的人,那么,我敢断言,动脑筋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动脑筋思考的人,是一种性格反常的动物。”并说“这至少是柏拉图的意见”。他认为文明的产生是有违人作为动物的天性的。同时卢梭也指出,人同动物一样都有感官,但除此之外,人还拥有“自由主动的资质”,即能够认识到自己是自由的。所以文明的产生又是必然的。事实上,有一个逻辑循环结构贯穿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全文:作为生物界普通的一员,人类生来便具有表现为“趋利避害”的应激性,可以将其理解为人类初始的“需求”,紧随“需求”而来的是各种欲望以及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恐惧感,由此寻找满足欲望和克服恐惧的方法。不同于大脑构造相对简单的动物,人们懂得如何运用逻辑和知识来思考和推理,而这无疑是一个使人类知识库愈发丰盈的过程。新的知识使人们不再满足于当下的生存生活状态,由此产生新的需求。周而复始,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进步。老子亦珍视自然状态下的人性,但同时对文明的批评似乎更甚:《道德经》里多有被后世学者诟病为愚民政策的论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第三章)。基于时代背景特点的思考,不应当把小国寡民理解为具体的制度构建——它应是一种原始的政治理想。
二人自然状态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理论逻辑进路各异,即方法论的不同。卢梭在理解人类自然状态时,是通过走进自然,亲身观察尚处于天性自然状态中的生物,从而进行推理的。老子则相对更为抽象一些,虽然也是以大自然为师,但其理论显然不是通过实验性质的观察,而是通过对宇宙、对万物的抽象思考得出的。究其原因,卢梭的思想可能受斯多葛学派的影响,斯多葛学派“虽然把财富,人间的显赫、痛苦、忧伤、快乐都看做是一种空虚的东西,但他们却埋头苦干,为人类谋幸福,履行社会的义务”(孟德斯鸠)。黄老思想本于《周易》,《周易》旨在理解宇宙运行的规律、行世间的大道。老子将《周易》的思想精华融入《道德经》中,创造了一个以辩证思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语即奠定了全书的玄学基调。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的自然法哲学思想有高深的思辨性,它不是以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或者指导社会变革实践为其理论功用,而主要是用来阐发人与自然主客体对立冲突中的思维演绎模式,因此具有向哲学辩证法与法学方法论演化的特征。
自然状态下政治乌托邦的构建
现代法治将人们从天然纯朴、人人平等的状态中剥离出来,为人们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生存环境与价值体系。自然状态的“稳定的时代”也许可以长久存在,但基于熵增的原理,即便再稳定的社会结构也容易被打乱,人类社会就需要在新的条件下达成新的稳定。故此,无论是对“自然”多么推崇的思想家,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个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回应。
卢梭继《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之后又出版《社会契约论》,正是要为人类设想出一种能够确保和促进人们幸福和美德的正义和健康的政治社会。综合考虑两本书的意旨,不难发现,所谓“自然状态”仅仅是卢梭心目中理想国家的参照物,实际上卢梭并不以“小国寡民”为其政治上的终极追求。伏尔泰曾批判卢梭,称其“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花这么多心思使我们变成野兽”,但他似乎并未充分理解卢梭思想的真正内涵。卢梭对社会真正的构想是:人类生存的天然欲望迫使他们形成集合体,集合体逐渐演变成国家。国家产生于人民的意志,因此其功能即在于保护每一成员。人生而自由,以自由的意志达成契约来建立国家,则每个人在新的社会模式(政治体制)下仍然能够保持自由与平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仍可称之为保持了“自然状态”,因为主权者不过是诞生于人们的共同意志之上,人们仍然是自由的。
从老子思想的角度来讲。稷下学宫创立后,诸子百家思想融合,黄老学派提取老子思想中入世的精华,进而阐释出一套治国之术,“援道入法”,从此形成了入世的哲学。但是老子本人的观点中入世的因素并不多,而是更为强调统治者的教化功能。“绝圣弃智,而民利百倍;绝仁弃义,而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未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道德经》第十九章)这里素来被诟病有愚民倾向。因为老子所欲构建的是一个人人内心清净、保持本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盗窃乱贼无从发生,犯罪恶行无从谈起。从这点来看,老子相较于卢梭,似乎更为消极一些。同时老子更加主张精神层面的自我治疗,对社会制度方面构想不多。
老子所谓“圣人”的统治,与卢梭论说中的“立法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如“圣人”和“立法者”都需要有天才的智慧,崇尚人人平等、一视同仁。但二者也存在诸多差异。首先,在卢梭看来立法者的功能是引导人们去认识和热爱公意,将自己视为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觉使个人意志服从于公意。而老子所谓“圣人”的作用,则主要在于“贵清静而民自定”,引导百姓培养清净、不争、顺其自然的心性,从而实现社会的和睦。另外,卢梭强调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公意”,而老子强调的统治者治国指导思想是“道”。“公意”产生于全体人民的意志之上,“道”则原本就存在于天地之间。一言以蔽之,一个是社会的合意,一个是客观的规律;一个归于政治功能,一个归于自然道德(天道,后演变为天理)。这是卢梭与老子政治乌托邦构想的明显区分,亦是自然状态理论在不同法哲学范式下演绎的本质思想差别,更是中西法律文明发展道路殊异的宏观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