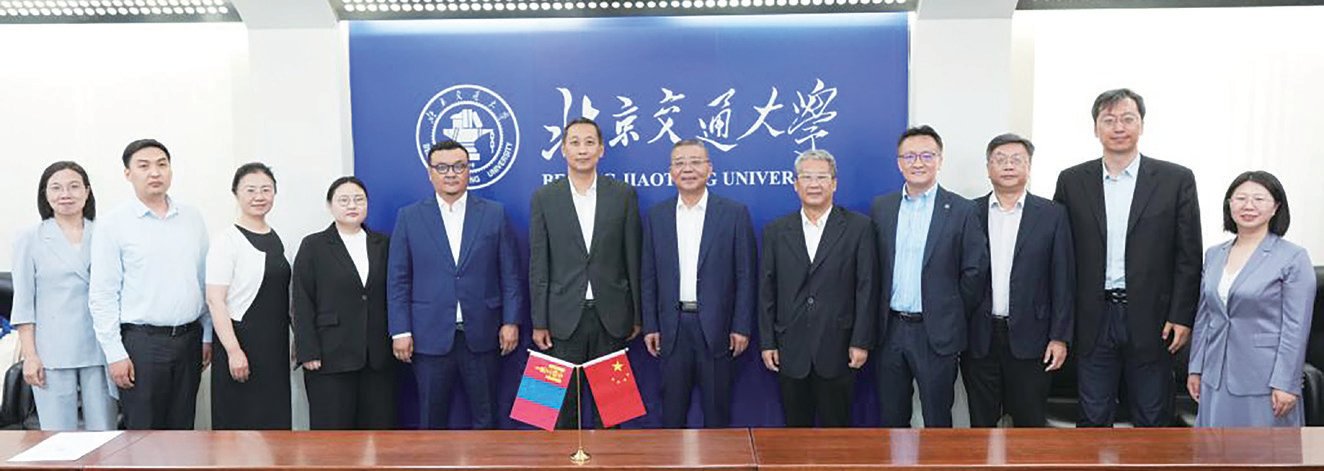我一直认为,爷爷和奶奶之间是没有爱情的。
在还没能完全摆脱封建桎梏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爷爷和奶奶的婚姻并不是自由恋爱的产物,而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怕共同育有一女二子,哪怕依偎着相伴了五十多年,哪怕与子偕老已经成为生活写照,爷爷和奶奶之间的感情却一直止于相敬如宾的缄默里。
我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自小也和奶奶亲近得多。更何况,对比精瘦硬朗、不苟言笑的爷爷,慈眉善目的奶奶总是更显亲切。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暑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
在我被时间偷换了的模糊记忆里,爷爷和奶奶是生活在平行世界的两个人。奶奶畏热,夏天里空调一定得调到最低,此外还要开着呼啦呼啦吹的大风扇;而爷爷畏寒,空调房里的温度他定是受不了的,所以一天里大半的时间爷爷都不在家,总是得空了便往外跑:或在大院里围观哪家老人对弈,或约三五好友去河边戏台看戏。总之,能在外就不往家里坐着。奶奶总爱熬夜睡懒觉,爷爷却习惯早睡早起。奶奶嗜辣,忌甜食;爷爷却偏爱甜食而不能吃辣。奶奶没读过什么书,识不得几个大字,一生只和柴米油盐打交道;爷爷却算半个文人,平日里总喜欢舞文弄墨。
我一直纳闷,相处在一个屋子里的人怎么能没有共同语言呢?可爷爷和奶奶却完全是向左向右的两条平行线,偌大的一个家,通常都只剩客厅里的电视机在咿呀作响。只有很少的时候,会夹杂着爷爷房间里收音机的哼哧声。
2015年夏日的最后一天,空气里的最后一点高温也随着飘零的树叶消失殆尽,奶奶也乘着风带来的那丝凉意走了。葬礼是爷爷一手操办的,一切都井然有序而又冷漠异常。葬礼上爷爷还是板着一副面孔,没有流露一丝表情,注视着跪在灵柩前哭到双眼通红的小姑,目光晦暗,良久才暗自走开。听着连绵不绝的哀悼声,敲锣打鼓的撞击声以及鞭炮噼啪作响的轰鸣声,我愤懑地想:爷爷是没有感情的怪物吗?不然,他怎么一滴眼泪都不流呢?
葬礼举办了三天,对我来说却像是一个世纪。直至站在那个黝黑冰冷的洞口,耳边不再充斥着让我作呕的奇怪声音,世界重新归于安静时,我才终于被迫相信:最终的诀别时刻来了,封上那个门,奶奶就真的与世隔绝了!
在白炽灯强光的照射下,落地玻璃折射出爷爷的身形——头发依旧梳理得整整齐齐,衣服依旧打理得干干净净,一双黑色皮鞋依旧擦拭得锃锃发亮。只是爷爷的脊背似乎不再挺直,佝偻着,像是再没有了支力。我看见爷爷胀得通红的鼻头,看见他年迈的脸上挤出的条条沟壑,看见他趴在玻璃上不断握紧又张开的手,还有,他那不知望向何处的双眼,已是布满血丝。几滴浑浊的泪,给他的眼睛蒙上一层迷雾,悲伤的气氛在他身上蔓延开来。
奶奶的离开没有阻止生活的继续,一切又被时间拨回正轨。爷爷拒绝了与子女一同居住的邀请,坚持一个人守着房子。那个没有了奶奶而空荡冷清的房子,让我有了一丝抗拒。直到高三结束的假期,我终于有勇气去揭开那道从未愈合的伤疤,再次回到这个地方,这座只有爷爷的房子。
尽管有着亲情的羁绊,我和爷爷却总是相对无言。餐桌上的话题无论从南还是从北,最终总会在奶奶身上戛然而止。我只好埋头吃饭,却被辛辣的辣椒呛了嗓子。我这才突然意识到,一桌四个菜,全是红油遍布——这是奶奶爱吃的菜。我突然想起,从进门的那一方地毯,到橱柜里碗碟的摆放,这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奶奶喜欢的模样。包括此时那个咿呀作响的电视机,呼啦呼啦吹着的大风扇,甚至空气里的凉爽劲,都与奶奶在时一般无二。
除了不见奶奶的身影,这个家一如从前的样子。爷爷也还是以前的爷爷,仍是面目刻板不苟言笑。却也不像以前的爷爷,没有了奶奶的爷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熬夜睡赖床,开始嗜辣,开始喜欢蜗居看电视,开始热衷于和柴米油盐打着交道了。
看着面前头发已开始花白的老人,我的心情像是盛满了柠檬汽水,突然就酸得冒泡,眼泪再也绷不住地兀自跑出。原来,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挂在嘴边。
在爷爷的爱情里,爱是无言,是迁就你所有与我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