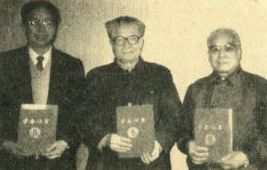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都把青年看作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朝气蓬勃的推动力量。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五四纪念日、青年节的讲话中,党的领袖和国家领导人都始终高度重视青年,指引着青年的出路。
1919年五四运动因外交而牵涉到内政,再涉及到一切社会问题,成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从1919年开始直到当下,五四的精神被增加、扩容,在每个时代都有新的时代精神被赋予、被希冀,在每个时代都指引着青年的走向,成为青年出路的引领者。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知识分子在五四发生后即追索五四的精神是什么,陈独秀认为必然是爱国救国。因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五四运动不同于之前的爱国主义的运动而表现出“特有的精神”:“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8页)。青年寻求爱国的途径也由五四变化为青年救国的自觉、自发以及直接参与和行动。同时,学生爱国的直接行动也为李大钊等其他青年领袖所共识,更赋予其新意: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领袖通过讲话引领着五四后已经觉悟的青年,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军阀强权政治的斗争。陈独秀认识到青年的爱国救国是需要指引的,1923年他对青年疾呼一定不要回避革命,要走革命的道路(陈独秀:《外交问题与学生运动》,《向导周报》第23期,1923年5月2日)。而李大钊期望青年应做的事已更多:“组织民众”“对现政局立于弹劾的地位”(《昨日之五四纪念大会》,《晨报》1923年5月5日)。毛泽东则呼吁青年要“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到工农民众中去”(毛泽东:《五四运动》,《解放》第70期,1939年5月1日)。在党的领袖看来,“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一定要发挥五四的时代精神,指引青年进行社会运动。
5月4日成为五四纪念日,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引青年、警醒青年的节日,因此也逐渐建立起以五四纪念日为主体的“红色五月”。1923年李大钊称五四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风纪之纪念日”(《昨日之五四纪念大会》,《晨报》1923年5月5日),1924年将五四纪念日认定为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更上升为“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指引青年“誓要恢复国家主权、洗清民族的耻辱”(李大钊:《这一周》,《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24期,1924年5月1日)。1924年瞿秋白指出五四运动从青年运动到群众运动,特别是从青年运动到劳动运动,在斗争的目标上也超越了民族主义而到社会主义,开启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潮(瞿秋白:《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五七———五四———五一》,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186页)。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看来,五四是中国民众第一次自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纪念日,领导运动的是青年学生,而组织领导青年的则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整个1920年代的党对青年前途的指引,在五四纪念的讲话中逐渐归结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在中国共产党力主发掘五四运动的青年价值的同时,每个时代都赋予五四新的文化和革命意义。
整个1930年代,特别是在日本侵华的大形势下,党根据抗战形势而提出新的青年的时代使命,逐渐归理出青年的出路在于全面地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青年要在抗战中充实、强健起来,担负起救国、建国的责任。在节庆等符号的构建上,党在各根据地逐渐建立起五四青年节,广泛宣传五四运动的救国精神,从而更加凝聚起青年救国力量。1939年毛泽东讲述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即将要转到胜利方面,最终要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因此,青年应该起到先锋、带头作用,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毛泽东:《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国青年》第1卷第3期,1939年6月1日)。周恩来勉励青年“贯澈抗战到底,勉为文化先锋”(《新华日报》1938年5月4日)。
1940年代的抗战中,在朱德、叶剑英等人五四中国青年节、国际青年节的讲话中频频号召全国青年继续发扬五四精神,团结起来参加抗战。叶剑英指出青年的出路“在战斗中显现出来”(叶剑英:《写给抗战中的青年》,《新华日报》1940年10月12日)。朱德号召青年担负抗战责任(朱德:《中国青年当前的任务》,《中国青年》第3卷第1期,1940年11月5日)。毛泽东为纪念国际青年节,题词“目前中国青年的任务就是打胜日本帝国主义”(《新华日报》1941年9月 7日)。董必武则称“打倒法西斯主义,扑灭东方的法西斯是中国青年首要的历史使命”(董必武:《纪念国际青年节》,《新华日报》1941年9月7日)。在抗战的艰苦斗争环境中,领袖的号召无疑指明了迷茫青年的救国之途。40年代中后期的革命斗争中,民主运动成为时代性主题,具体落实到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与反动势力斗争上。
1949年在走向新中国之际,青年走向光明,也象征着新生中国的希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富强、繁荣的民主主义新中国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毛泽东号召青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勉励青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毛泽东:《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页)。改革开放之初,华国锋等人希望青年站在时代前列,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革命传统,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华国锋:《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5月4日)。1984年习仲勋号召青年奋起改革,以大无畏的创造精神献身于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改革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青年们应该坚持的正确方向(习仲勋:《发扬“五四”光荣传统,做最富有创造精神的新一代》,《人民日报》1984年5月 4日)。1986年他又寄青年以希望:积极参加改革、出色做好本职工作、踊跃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觉同工农相结合(习仲勋:《对青年的几点希望》,《人民日报》1986年5月4日)。对于青年的重视上,邓小平勉励青年一代要争当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江泽民勉励青年继续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担负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贡献毕生精力(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人民日报》1990年5月3日)。1993年胡锦涛的讲话中,提出广大青年一定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同全国人民一道,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胡锦涛:《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人民日报》1993年5月4日)。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在讲话中勉励青年承担起各行各业的突击队作用,发挥聪明才智、尽情展现人生价值,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服务。
新时期,国家领导人也十分注重青年出路的指引。2013年习近平指出青年在近代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历史与现实证明,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5月5日)。新时期,国家领导人对青年的号召,无论从青年个体的生命历程,还是国家的整体命运,都能体现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之延续,这依然是今天我们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指引着青年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把握人生的际遇与机缘,弘扬五四精神,担当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历史重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各个时代领袖、领导人的讲话,体现出五四的青年出路无外乎救国、建国,以青年使命之担当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命运。党的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的五四青年工作讲话可以是公开的演讲,也表现为在公共媒介上发表的文字,更有以文件的形式对青年进行劝勉、启诱,也有题词、口号等简短而有力的直接号召,这些都可以视之为五四讲话的范围,在每个时代都具有对青年出路的探索和指引的价值和意义。编辑者从舆论报刊、领袖文集选集、党的文献等中,整理出党的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的部分五四讲话,编辑成册,按照时间顺序排比,使阅读者能够从时序中梳理五四讲话中党的领袖所赋予的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的原始、发展、提炼的过程性。这一编年文本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百年记忆史的一个独特视角,不但对百年“五四学”有了一个基本端详,也对以青年为主体、以青春为主题、以励志为鹄的的时代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重读这些“讲话”,对激发当下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入世创业也极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