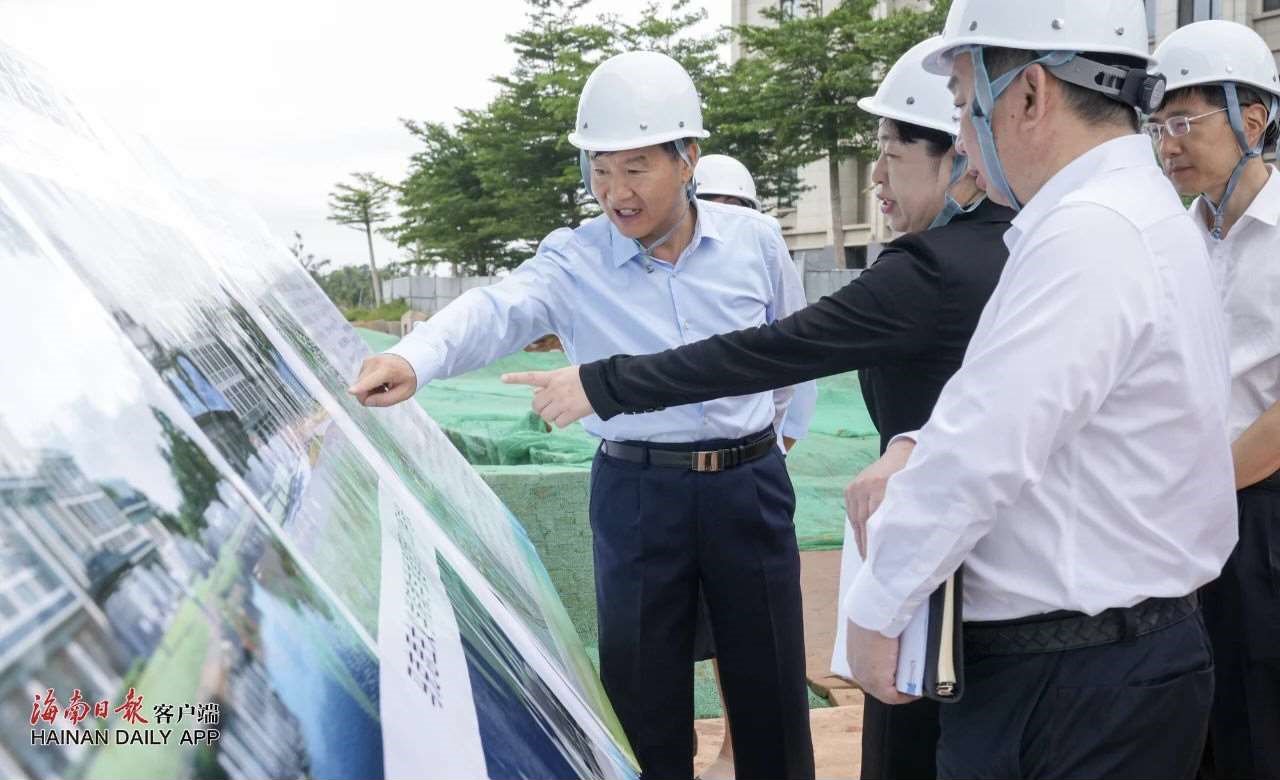冬之语丝
冬天,我常站在雨雾缭绕的山冈上,静静地平视远方。冬天的心似乎想着:“我虽然没有春天迷人的笑靥,也没有夏日奔放的性情,更缺少秋天明星般的风采,但我有冰清玉洁的心灵啊!他们时常无视我的存在,还怨恨我对事物看法的冷静而不愿出门以视反抗,即使出门也只将裹得厚厚的身子交给雾霭、雨雪、冰凌。一些植物,被誉为岁寒四友的梅、兰、菊、竹是我特别喜欢的;而我也在人世的轮回中把它们看作具有高尚气质的时代楷模,号召一切愿意上进的动物都应该如它们那样不畏风寒、不惧冻裂,始终保持昂扬的意志品质,将花的芳香和叶的翠绿留在凄厉的寒霜里。我的国度里总爱下雪,雪总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低低的调儿展示洁白无瑕的温柔,以讨得诗情画意的钟爱,把我苦心营造的阵地强行夺去。还有那冰凌也是到处争宠,将冷冰冰的脸儿扮成花儿似的笑容,也分得了不少羡慕的眼光和赞叹的话语。留给我的除了老人的伤感和颓废外,已找不见了青春的姿容和火热的情怀,但是我还是愿意秉承成熟的意愿把生命的美好递给下一代,并任劳任怨、乐此不疲。"
常常流露出怨恨那种灰色情绪,将脸铁青着,虽是真诚友好的,仍令人不敢接近的冬天,借了风的灵性从南方秀色可餐的山川来到了北方粗犷奔放的土地。风儿的翅膀在飞翔的旅途中撞击了冰岩的坚实,一滴滴的血融入高原、平地、草原、戈壁、沙漠,旋即就凝集成了冰的色调。但是受伤的风儿依然哭泣着坚强地前行,它碰着了白杨树,它看见摇摆着挂在白杨树上的枯黄树叶,就顺手卷起又用力扔向到处铺满冰块的贫瘠土地。虽然整个大地都被瑟瑟的寒风所控制,白杨树仍用耿直得近乎傻的手臂直直地指住哭丧着脸的苍穹,并勇敢地告诉世人忧愁的天气是培养自己成熟性格的最佳伙伴,白杨树便被打造成了钢筋铁骨的战士,静默地守卫着一方牢固和厚实。然而世人往往忽视了白杨树建筑起的房屋始终比南方的房屋温暖的事实,由事实释放的情感打动了冬天的心房,冬天便在北方找到了刚直不阿的气质。其实北方的冬天也有叛逆,是对冰的叛逆,是对荒凉的叛逆,是对肃杀的叛逆。这种叛逆不就是对生命本色———绿色的追求么!
冬天又回到诗人的情怀,翻开了古人的诗篇。翻啊翻,却很难看到关于自己的感叹和赞美,不是歌唱明媚春天的篇章,就是颂扬热烈夏天的佳句,更多的是秋天的诗语般的海洋。比如说吧,李白就特别钟爱春天,《春思》、《春日行》、《春日独坐寄郑明府》、《春日游罗敷潭》、《春日归山寄孟浩然》、《春滞沅湘有怀山中》等。而杜甫呢又尤其青睐秋天,《秋兴八首》、《秋野五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步一枯荣”也是三岁小孩都能背的。歌颂夏天的也不少,如白居易的“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李商隐的“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杜甫的“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等等。这种诗坛现象显然是不公平的,是对冬天的仇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赞美岁寒四友以及冰、雪的诗篇远远超过了春夏秋的总和,就让这些儿女去表现吧,让它们去展示青春、展示风采,把美留到世间、留到生活。
在北方时,对北方冬天的单一有了透彻的了解,自然向往着南方冬天的复杂与朦胧。在南方时,又对南方冬天的阴霾有着烦躁的认识,敞开心灵又想拥抱北方冬天的纯洁和明媚。是不是生存空间久远所带来的厌倦和不满呢?去了记忆的长河里漂流,却只能抓住岸边真实的巉岩,而不能把住水中的空蒙和眼前的虚幻。这种差异的美不正如思想飞跃的琴音紧贴时空的耳壁在逡巡么?每一首华丽的乐章都会越出疆界的阻隔,地域的限制,最终以优美的图画保存在历史的记忆里,不会发黄、不会变质,仿佛冬天的本色一样,生长着绿,积蓄有暖,用心灵的美唱响永恒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