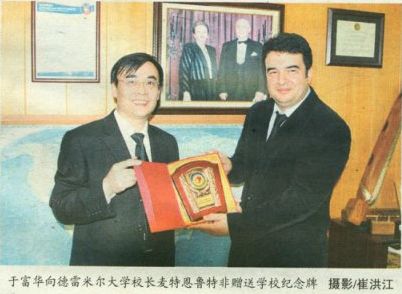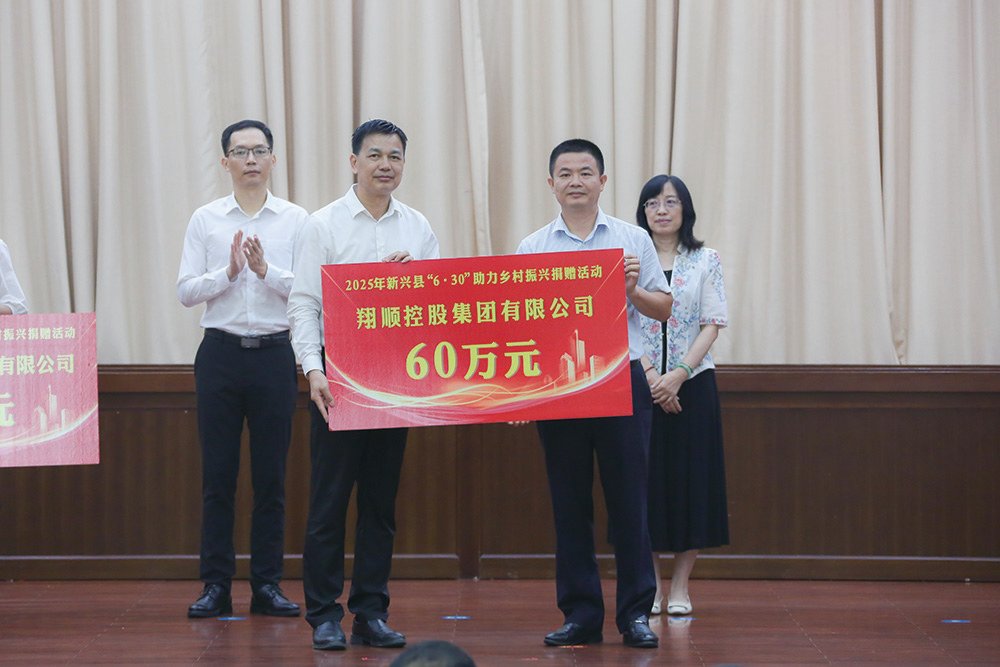青丝华发一灯红——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有感
方卫平
日前,“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在精业楼报告厅举行,我国语文教育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王门弟子为此盛会献上的一副对联“砚海耕耘积八百万字,乐在攀登,高度基于广度深度;杏坛弦诵历四十九年,甘作奉献,立言总为立人立心”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我曾受尚文先生之邀,参与编写《新语文读本》小学版;后来,他又应邀出任儿童文化研究院顾问。此时此刻,对他的为人治学,我确有不能已于言者。
在我国语文教育界,王尚文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卓有建树的大家。他的《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语文教育学导论》《语感论》等一系列著作,已经成为我国当代语文教育界的重要思想财富。尚文先生认为,人的发展应该是向“人”的生成过程,教育是促进这一过程的一种重要途径,而语言和文学的教育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发展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可以说是一切教育的基础。这是他关于语文教育的基本理念,也是他从事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的根本动力。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就在深刻反思1949年以来我国语文教改的历程后认为,当代语文教育发展历程中曾有以片面强调政治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一浪潮和以片面强调工具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浪潮;但他坚持认为,语文学科必须努力书写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字,它绝非工具学科,而属人文学科,因此,他提出应当掀起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浪潮。为此,他著书撰文,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直至九十年代末期,他的观点才逐渐得到广泛认同。《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称其为“语文教改第三浪潮的引领者”。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人文性理论,是关于学科性质的规定,强调在语文教育中要以人文激活语文,在语文中渗透人文,必须以语文为本体,以人文为灵魂,而不是抛开语文讲人文,把语文课上成不见“语文”的所谓“人文课”。但出乎意料的是,后来却出现了所谓“非语文”、“泛语文”现象,于是他又在《中国教育报》《课程·教材·教法》《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等报刊发表文章,多角度、全方位地论述了语文与人文的关系,指出人文原在语文之中,而不在语文之外。尚文先生的努力为语文教改的健康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尚文先生都作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具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例如,他在夏丏尊、叶圣陶等前辈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语感中心说”。上海师大王荣生教授认为,它彻底地扭转了研究语文教学问题的思考方向,因而“成为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奠基石”。他那数十万言的《语感论》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前后共出三版,足见他在学术上不断自我超越的坚定追求,也可见该书影响之大。又例如,他首先将对话理论引入语文教学,由此提出关于语文教学的“对话性”理论。它既非对话理论的克隆,也不是为语文教育穿上一件新的外衣,而是哲学解释学与语文教育对话的结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我还想特别提一下尚文先生关于文学教育的观点。他始终认为语文教育是语言(汉语)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复合,复合不是混合,两者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就好比是田园和花园,不能相互取代。关于文学教育,他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著名比喻:文学是青少年身上的“通灵宝玉”,不可须臾或离。他甚至认为,文学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在一个国家教育中的地位,其实就是“人”在一个国家中、在一个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的折射。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区分了“文学的教育功能”和“文学教育的功能”这两个既有交集又互不相同的概念,认为不能把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或混为一谈。他说,我们不能把文学教育单纯地当作发挥文学教育功能的舞台,或者以实现文学的教育功能为文学教育的主要目的。由于中小学语文课程所占的时间本已不多,用于文学教育的课时更加有限,要让文学在这局促的时间内全面实现它的教育功能,势必捉襟见肘。但文学教育的宗旨主要并不在于教学生读多少文学作品,而在于唤醒学生对文学的渴望,点燃学生对文学的热情,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这才是文学教育的功能。他的上述观点引起了我的深思,颇受教益。
在我们共事的过程中,尚文先生的事业心、使命感给我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编写和修订《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那几年,从冬到夏,从早到晚,可以说,他的兴奋点一直在《读本》的编写上。集中开会时,甚至在饭桌上、散步时谈的也主要是读本的编写问题;有时半夜醒来想起什么,就立刻起来奋笔疾书。他那一丝不苟甚至显得苛刻的态度,成为大家的楷模。他对编写组的年轻人既亲切又严厉,晚辈们爱他敬他,多少也有点“怕”他。编写组同仁都觉得无论是为人还是治学,都深受他的教益;而尚文先生却总是一再对我说:“我们这支编写队伍非常理想,尽管有的人年纪很轻,我还是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些年来,我们跟《新语文读本》一起成长。”
尚文先生早年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曾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过关于李白的长篇论文。该文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收入《李白研究论文集》一书,其中论文作者都是如闻一多、俞平伯、朱光潜这样的知名大学者,只有他是二十来岁的无名小卒。我原来早就知道他于古典文学很有造诣,写得一手好诗词。在编写《新语文读本》小学卷时,我才发现原来他的外国文学功底也很深厚扎实,谈起有关话题,总是旁征博引,如数家珍,让人佩服不已。
尚文先生常说做学问就是做人。在编写《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过程中,他既是我们编写团队的灵魂人物,又从善如流,乐于汲取他人有价值的意见,唯独稿费分配,他大权独揽。从绝对数看,他当然属最高等级,但与其他同仁的比例看,显然他是拿得太低了。我当然向他提出了我的方案,提高他的比例,但他一直固执己见,凭我怎么说,他都不听。他说万事唯求心安而已。诗言志,我喜欢他的诗词,“沧海桑田明月在,青丝华发一灯红”是我最喜爱的句子之一,因为这是他的赤子之心的真实写照。“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谨以此先贤名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