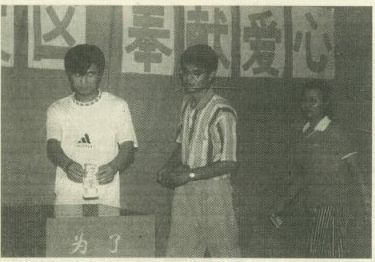春归如过翼。晴暖的立夏日一到,就渐渐迎来灿烂的夏天。今年的立夏在阳历5月5日,恰逢东邻日本的端午节,而中国己丑年的端午是在阳历5月底,小满过后第七天。五月端午是中国人最具特色的传统节日之一,作为端午节文化符号最重要的元素,我们所有人对屈原的认识应该都是从端午节开始的。青翠葱茏的五月天,伴着窗外玉兰树上初开的朵朵洁白玉兰花,阅读缤纷千年的楚辞,真是一件情理相宜的赏心乐事。
屈原的作品,向来称为 “楚辞”。无论是作为特定地域的文学,还是极具个性特征的文体,楚辞和屈原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无从分离、血肉关联。翻览楚辞,虽有两千多年的时空阻隔,那古奥的楚声楚语仍然疏离不了我们对屈原的感悟;而那一年一度不可或缺一如既往的五月端午,也在永续活现着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不朽形象。唯美的屈原,唯美的楚辞,是我重温楚辞领会楚辞的关键词。
唯美的屈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理想主义者。他满怀高远的政治理想,一方面始终以内修美能、清洁之行规范自己,另一方面是对 “美政”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一生从不愿 “变节而从俗”,虽明知这样“固将愁苦而终穷”,但仍然持守“虽九死其犹未悔”、 “岂余心之可惩”的独异的不屈信念。千古 《离骚》描画的是理想主义者痛苦的心路历程,抒发了唯美追求却不合时宜的种种抑郁不平。如果说 《离骚》是一篇恢弘壮阔的人生自述,那么《九章》中的九篇作品则让人一一感受特定时段屈原被谗见疏的情状和忧伤,这里既有橘树 “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的体物写志式的理想憧憬,又有 “忠何罪而遇罚”理想遭挫的烦闷;从 “魂一夕而九逝”的首次流放,到 “独茕茕而南行”的再次放逐,屈原始终抱定着 “不能变心而从俗”理想意念。阅读屈原自沉之前的作品 《怀沙》,我觉得开篇的句子: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应该就是端午节的最早氛围背景。
唯美的楚辞是一部彪炳千秋的缤纷文学读本。辞藻华美、铺饰纷繁、想象浪漫,唯美表现手法无处不在。作为一个杰出的优秀诗人,屈原创造性地把崇高伟大人格和芳洁坚贞艺术形象完美融合: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篳以练要兮,长閦颔亦何伤?”以 《离骚》为标志的芳草美人比兴寄托手法,开启活化了中国文学两千多年来的唯美文学意识。而 《九歌》十一章所洋溢的出神入化、奔放奇幻的神话色彩,不仅拓展了中国浪漫文学的想象领域,而且含蕴着丰富的幽渺柔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意趣,那在 “??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衬托着的湘夫人的幽怨和哀伤; 《山鬼》开篇描绘的景象: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都是一幅幅永远填充不满的审美奇丽空间。
品读唯美的楚辞,自然会触及唯美的屈原创作的主体意识,而《天问》应该是绕不过的文本。 《天问》是一篇古今罕见的奇文,是楚辞中最错综变幻、纷繁耀眼的篇章,一百七十多个问叹连缀成篇,问天问地问人世兴衰,具有空前的人文理性色彩。屈原在流放山泽之际,看见楚国宗庙祠堂中一幅幅关于天地山川、神灵怪异的壁画,有感而发, “题图书壁”而成的 《天问》,虽然留下许多 “文义不次”、 “多奇怪之事”的谜团,但其呈现出的宏阔视野、终极思索和人文关怀所具有的理性维度,在楚辞中是无与伦比的。现代意识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本质上是自由与理性的互衬互补,从这个意义上读 《天问》、读楚辞,说屈原是 “自由的思想、独立的品格”的先驱,应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