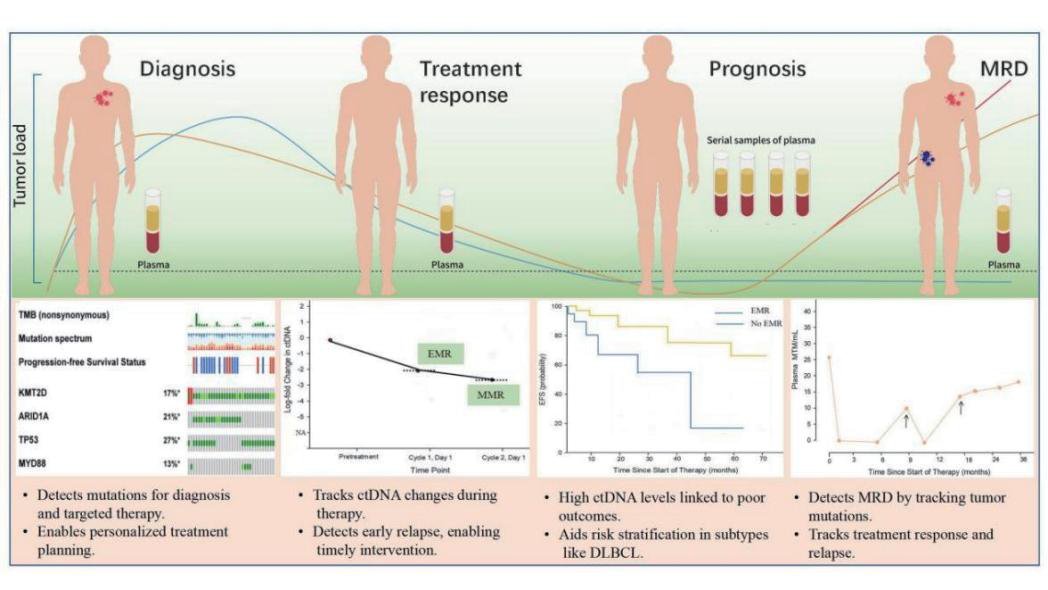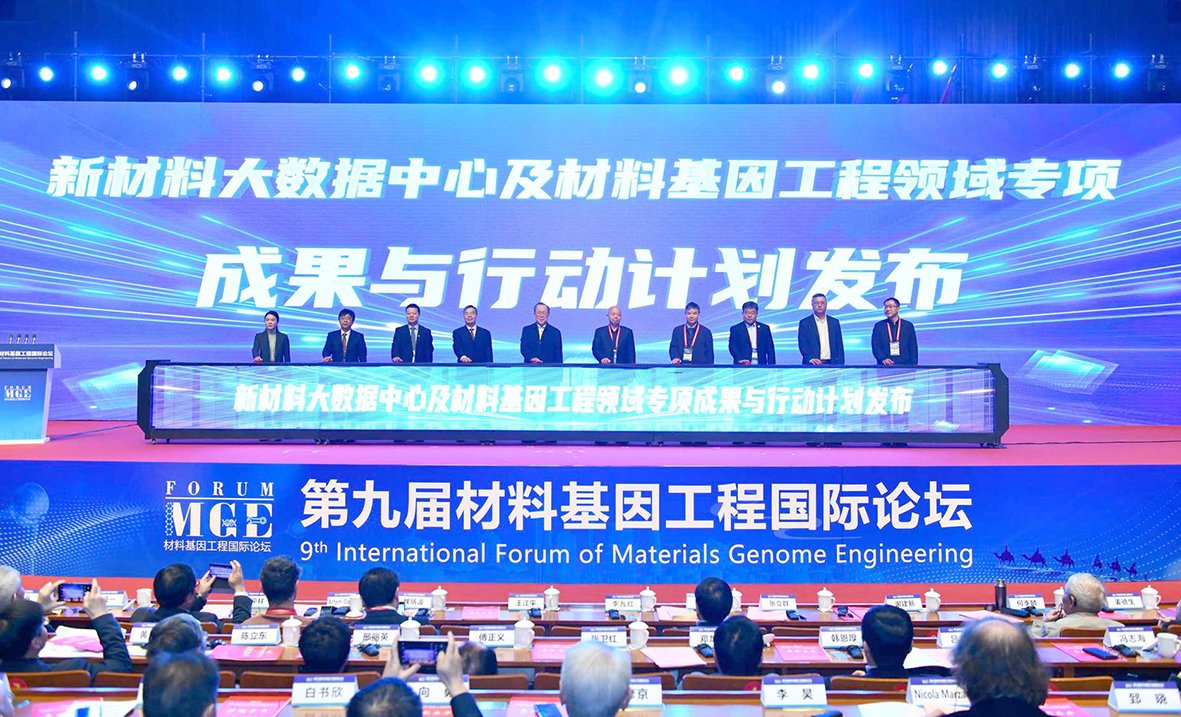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人们还有多余的时间去读经典,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吗?对于重读经典的现实意义,人们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去理解,而我则想从阅读经典对今天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何启迪意义的角度谈一些认识和看法。
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重要著作的写作动机和著述风格来说,只有阅读经典,才能真正理解和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这种与时俱进意味着它始终是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和发展。改变自身就意味着它不会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永不过时的永恒真理,而是面对实践的变化和发展不断地修订和补充自己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都是黑格尔的信徒,也都曾是费尔巴哈的坚定信仰者。然而,随着他们在社会现实中的实践以及他们思想认识的变化,他们敢于不留情面地对那些已经过时的理论进行大胆地批判和抛弃,其实就是敢于大胆批判和抛弃自己头脑中已经过时的不适用的理论,这就为他们提出新思想新理论扫清了障碍,推动了他们思想的与时俱进。纵
观整个马克思主义诞生早期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体现这一历史阶段的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经典著作,可以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清理自己旧思想旧理论的过程。这种清理不仅没有使马克思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却更加增添了这种理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当今时代,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许多新问题新现象是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伟人也未遇到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的。寄希望于所有的问题都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思想和理论里找到答案,不仅是一种徒劳的懒惰行为,而且也是给马克思、恩格斯出难题。我们只有结合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分析新问题,抛弃旧观点,总结新理论,敢破敢立,才能真正应对时代的挑战,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落到实处。
因此,只有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才能够使我们真正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并真正使这一理论品质得以体现。
其次,我想谈谈应该如何读经典。
对经典的阅读从来都有两个基本路径:要么老老实实“回到经典文本”,要么“让经典来到当代”。中国古人称之为“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我们认为,对于经典,无论是“我注”还是“注我”,本质上差别不大,因为这里的主体都是“我”。
我的看法是,阅读一部书籍,尤其是经典的重要理论著述,需要的是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解读方式。解读经典著作时,非要追求形成特定的共识和统一的定论,既是不合适的,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试图寻求文本的所谓客观原意,如同建造一座“巴比伦塔”,最终只能作鸟兽散。古今中外还没有一部经典著作的文本价值能够被宣称
已被人们诠释完,并形成完全一致的所谓共识。任何文本只有在不断地解读中才会发现其中深藏的奥秘。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经得起任何时代、任何立场、任何人物对它的阅读和解读。而该经典也会随着不同时代人们对它的不同解读而不断迸发出新的价值。
哲学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特定时代的读者在解读既定的历史文本时,他在接受时一定会带着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他那个时代所关心的问题,他那个时代的所谓“偏见”和“热情”,以及他个人知识的“先见结构”和“新的视界”。如此一来,当他的“视界”与作者的“视界”相“融合”时,他将会用自己新的眼光,带着自己新的问题去接受它、理解它、评价它并重新创造它。正是历史中这种永不消失和永不重复的“现代视界”使艺术接受中的创造和评价能够在无限的历史演绎中展开和丰富。艺术作品是如此,理论著述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亦是如此。
所以我主张在读经典时,时刻不要忘了阅读者当下的语境,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以及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要解决的问题。只有把经典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才会发现经典的魅力所在。也只有如此解读,才能不断让经典焕发出新的价值和意义,迸发出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因此,读经典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意义再生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仿照哲学家卢卡奇的话就是:在读经典时,即便我们最终不得不抛弃经典里的思想和主张,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是一个经典的维护者和继承者,因为我们坚持了经典里的方法和原则。
所以说,读经典为我们创造了一次理论再造和意义重生的绝佳机会。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多读一些经典呢?